
《影迷》
记忆,连接的不仅是过去的自我,更是人类共同的经验。它决定了我们如何理解自身,也决定了文明以何种姿态延续。
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眼中“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厄普代克所言“就在我们身边但令我们琢磨不透的巨人“,切斯瓦夫·米沃什,将一生中无限的文字,献给他的故乡城市维尔诺,献给他的记忆。
对于米沃什而言,失去记忆意味着堕入虚无,其危险不亚于对自然环境的毒害。而我们所有人,都是过去与未来的纽结,必须承担起记忆的重任,接过历史,尽可能如实地讲述。
米沃什的一生见证了二十世纪的诸多恐怖事件:“二战”、纳粹大屠杀、白色恐怖……他活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最后,他将记录一切。他的 《在时间的荒原上》与《米沃什词典》,即是两本不同形态的记忆二十世纪之书:
前者是米沃什跨越三十年的自选散文集,游弋于文学、神学和哲学的边界,思考诗歌、时间、现实、罪恶、幸福等命题——民族主义、诗歌写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督学等——提供一种敏锐的、毫不妥协的叙述,打破我们心灵的禁锢;
后者则以词典的形式,以浓缩高度智性和深沉情感的词条——加缪、波伏瓦、薇依、布罗茨基等——追忆那些走向消散的声音和面孔,呈现出20世纪历史文化广阔的精神地图,建起我们通往过去的、有血有肉的桥梁。
在虚构与失忆不断被制造的今天,米沃什的文字是我们共同拥有的一座记忆宫殿,带领我们走向更清晰的复杂世界。
《在时间的荒原上》
诺贝尔获奖致辞
随着大众传媒不可思议的飞速发展,我们日益缩小的星球正在见证一个无法定义的进程,它的特点是拒绝记忆。当然,千百年来,占据人群主体的文盲对各自国家和文明的历史知之甚少。而当代的文盲能读会写,甚至还在学校里教书。对他们而言历史虽然存在,却是模糊的,是一种奇异的混乱形态。莫里哀成了拿破仑的同代人,伏尔泰成了列宁的同代人。
更有甚者,过去几十年发生的事件如此重要,对它们的认知或无知将决定人类未来的命运,然而它们却在消散、褪色,失去了连贯的逻辑,仿佛弗里德里希·尼采对欧洲虚无主义的预言真真切切地实现了。“虚无主义者的眼睛,”他在1887年写道,“不忠于自己的记忆:它任由记忆失落、凋零……他不为自己做的事,也不会为人类的整个历史而做:他任由记忆凋落。”
今天,我们被关于过去的虚构包围,这些虚构违背常识,有悖于我们对善恶的基本认知。《洛杉矶时报》近日有篇文章说,否认发生过纳粹大屠杀、声称那不过是犹太人捏造宣传的书已经超过一百本,各种语言的都有。如果连这样疯狂的事都是可能的,难道大脑就不可能永远彻底失去记忆吗?它带来的危险,难道不比基因工程和毒害自然环境更甚?
三十年海外生涯中,我感觉自己比西方的同事(不论是作家还是文学教师)享有更为有利的条件,因为不论是最近还是许久以前发生的事,都在我的头脑中呈现出轮廓清晰而准确的形态。
西方受众遇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或匈牙利的诗歌、小说或电影时,也有可能凭直觉感受到类似的敏锐意识,它长期对抗着审查制度施加的种种限制。因而记忆是我们的力量;它帮助我们抵抗一种话语,当那种话语不能在树干或墙壁上找到支撑,就如常春藤一般重重缠绕。
几分钟前我说过,我想要消除矛盾,弥合诗人对距离的需求与对团结人类同胞的渴望。但如果我们把诗人这一职业比作在地球上空飞行,就不难发现其中必然包含矛盾,在那些诗人相对较少落入历史陷阱的时代也是一样。毕竟,怎样才能既翱翔于云端,同时又看清地球上的每个细节?
不过,在岌岌可危的对立均势之中,借助于时间流逝所造成的距离,一种平衡得以实现。“看见”不只意味着眼前所见。它也意味着在记忆中留存。“看见与描绘”也可能意味着在想象中重构。
由于神秘的时间而获得的距离,不应让事件、风景和人物变作越来越淡的一团影子,相反地,它应该使它们显露无遗,使得每一个事件、每一个日期都意味深长,并作为人类堕落与人类伟大的永恒标记而持续存在。生者从永远沉默的逝者手里接过一份嘱托。只有准确地如实重构那些事,从虚构和传说中挽救历史,他们才算完成了使命。
于是,在永恒的当下被俯瞰的地球,以及在重新找回的时间中长存的地球——它们都能成为诗歌的素材。

《一个半房间,或回到祖国的感伤旅行》
如今有一种深刻的转型正在进行着,对此我们几乎毫无察觉,因为我们就身在其中,但它时不时会通过一些震惊世人的现象浮出水面。借用奥斯卡·米沃什的话来说,这种转型与“空前活跃、生机勃勃、饱受折磨的劳苦大众最深的秘密”有关。他们的秘密,一种对真正价值的隐秘需求——找不到自我表达的语言。在这方面,不仅大众传媒,知识分子也要承担起深重的责任。
然而转型还在进行,让人无法做出任何短期预言,而且,尽管有这些恐怖和危险存在,我们的时代依然很可能是人类上升到新的意识层面之前所必经的艰苦时期。之后将会出现新的价值序列,而我相信自己曾潜心研习的西蒙娜·薇依和奥斯卡·米沃什会收获他们应得的认可。我觉得我们应该公开承认自己对某些人的倾慕,因为比起指出那些我们激烈反对的人,这种方式更有力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
由于诗人的职业恶习,我的想法迂回曲折,但我仍希望在这次演讲中,我的是非观表达得足够明确,至少在继承对象的选择上是如此。因为我们所有在场的人,不论演讲者还是聆听者,都只不过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纽带。

《乡愁》
《米沃什词典》 跋
DISAPPEARANCE, of people and objects
(消失的人和物)
我们生活在时间之中,因此都服从于这样一条规律:任何事物都不能永远延续,一切都会消逝。人会消失,动物、树木、风景也是如此。正如所有活得足够长的人们所知道的,就连那些关于曾经活过的人的记忆也在消亡。只有很少一些人会保留他们最亲密的亲人和朋友的记忆,但即使是在这些人的意识里,面孔、姿势和话语也在逐渐消退,直到永远消失,再也不会有人出来作证。
对坟墓另一边那个世界的信仰,全人类都是如此,这种信仰在阴阳两界之间划了一道界线。两界之间的交流是困难的。在被许可下到阴间去找寻他的爱人欧律狄刻之前,俄耳浦斯必须答应几个条件。埃涅阿斯是因为拥有某些魔力才得以进入地狱的。那些居住在但丁所描写的地狱、炼狱和天国里的人们不曾离开他们死后的住处,告诉生者他们在那里的情形;为了了解他们的命运,诗人但丁必须走访死者的国度。先是由维吉尔,一个幽灵引领——因为他在很久以前就死了,然后由贝阿特丽切引领,她居住在天国。
纵然如此,在那些相信万物有灵、相信祖先庇佑的人们看来,分隔两个世界的那条界线并不完全分明。死去的祖先继续住在家园或村子附近的某个地方,尽管我们看不见。在新教教义中,他们已经没有存身之处,没有一个新教徒会向死者寻求帮助。天主教则不然,它引入替人祷告的圣徒形象,增加圣徒的数目,扩大宣福的规模,以此来表明善灵们并未离开生者,天人永隔。正因为此,波兰的“万灵节”尽管起源于远古时代野蛮人的万物有灵信仰,但却受到了天主教会的祝福,被看成是一种重要的替信徒祈祷的仪式。
密茨凯维奇相信幽灵的存在。他在青年时代曾是个伏尔泰主义者,似乎开过幽灵的玩笑。不过,即使在他翻译伏尔泰的《圣女贞德》时,他也选择了贞德被强暴受辱,以及作恶者在地狱里领受应得惩罚的场面。他的《谣曲集》和《先人祭》可以用作通灵手册。后来,他不就劝告人们要在生活中有所作为,因为“没有躯体的灵魂难以行动”吗?更不必提他讲述的那些灵魂被惩罚进入野兽身体的故事,那些故事显然是从民间信仰中借来的,或者来自卡巴拉主义者信仰的轮回转世说。
取自白俄罗斯的先人祭仪式,最有力地证明了生者和死者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因为生者会用极为世俗的方式向死者祭献食物,以此召唤死者的幽魂。密茨凯维奇在《先人祭》以及其他一些作品中,写到过阴阳两界的相互作用;在他笔下,阴间没有不可改变的事物。
人一个接一个地消逝,于是问题越来越多:他们死后是否还存在?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宗教空间连着历史空间,被理解成文明的传承。比如,某种语言的历史会呈现为一个地方,我们能在此会见我们的先辈,那些一百年前或五百年前用我们的语言写作的人们。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甚至说,他不是为未来的人们写作,而是为了取悦那些诗歌先贤的阴魂。也许,从事文学写作只不过是“先人祭”的一种永恒的庆典仪式,是对祖灵的召唤,希望他们会显形片刻。
波兰文学中有些名字一直活跃在我心中,因为他们作品的生命力至今依然;有一些则不那么活跃了,还有一些拒绝再出现。但我所考虑的不仅仅是文学问题。我的时代,我的二十世纪,重压在我的心头,它是由一些我认识或听说过的人们的声音和面孔所构成的,而现在,他们已不复存在。许多人因某事而出名,他们进入了百科全书,但更多的人被遗忘了,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利用我,利用我血流的节奏,利用我握笔的手,回到生者之中,待上片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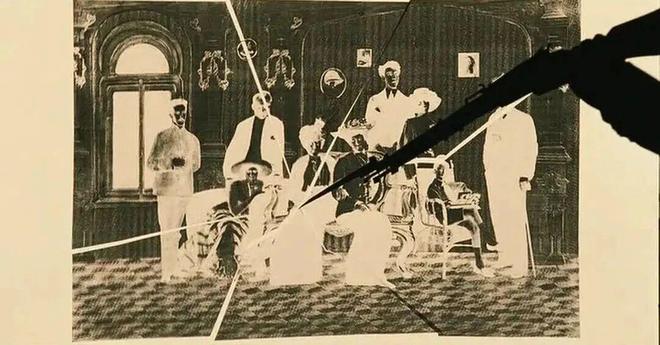
《一个半房间,或回到祖国的感伤旅行》
在写作这部词典的过程中,我常想,我们最应该做的,是深入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命运的核心,而不是把自己局限在一些外在因素上。书中写到的人们往往通过一些并不特别重要的细节一闪而过,对此他们只好知足了,因为即便以这种方式被记住,总好过彻底被遗忘。
也许这本词典是一件替代品,它替代了一部长篇小说、一篇关于整个二十世纪的论文、一部回忆录。书中所记的每个人都在一个网络中活动,他们相互说明、相互依赖,并与二十世纪的某些事实相关联。由于傲慢(看起来肯定如此),或由于故意的散漫,我遗漏了一些名字;说到底,我并不为此感到遗憾。
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20世纪最重要与最恐怖事件的目击者,
创新兼反叛的思想者与触角
直抵问题核心,径直作出回答
”要存活于这个时代,只有通过吸收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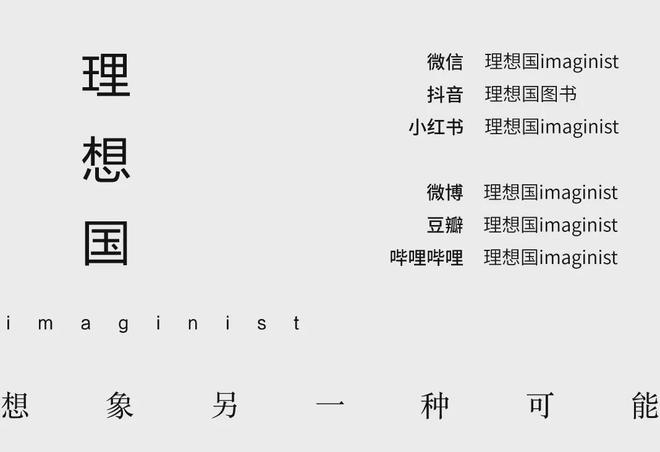
 晋ICP备17002471号-6
晋ICP备17002471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