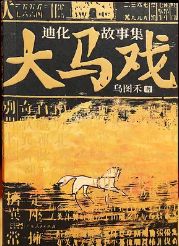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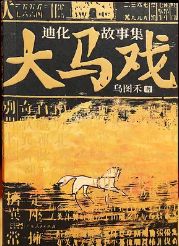
一
2020年,我在成都屋顶上的樱园(一间文艺餐厅)开设的写作工坊,学习写作。授课老师是何大草先生。每个同学必须在学期内交一篇小说,主题是故乡。
我一连交了两个短篇。何老师点评说:地方和人物的异质感、陌生感不够。
我心里在嘀咕,乌鲁木齐有啥陌生感啊,和成都也差不多嘛。都是城市。
对于乌鲁木齐,我只熟悉为数不多的几个地方。
我家在北门。大西门、小西门,有几条街的服装批发市场。小时候,母亲一直带我在那儿买衣服。南门有一个很大的新华书店。大十字、小十字的商场多,逢年过节会和家人一起去逛逛。二道桥的巴扎,家里来了外地客人,父亲都会带去转一圈,买点干果、维吾尔族人打的手工小刀。平时和家人、朋友游玩的地方很有限,西公园、红山。
有一次,我和父母闲聊,听父亲说起以前他和我的爷爷一起去看大马戏的事儿。父亲说,两个人走了一夜,从他出生的地方,一个叫长山子的村子,一直走到乌鲁木齐。
我问他,最后看到啥了?马戏好看不?
父亲说,哎,哪儿记得那些,应该就是些猴子啊、马啊,都记不得了,可那条路真是够远的呢,现在想起来脚还觉着疼呢。
七十多岁的父亲说着,嘿嘿地笑起来,像个孩子。
《大马戏》是我父亲的故事,也是我的。
它叫我想起了18岁离开故乡的第一晚。那时候,从乌鲁木齐到成都,坐火车要三天四夜。我白天一直坐在窗边,盯着外面看。戈壁滩一眼望不到头,火车像是永远都开不出去了。晚上,我听着过山洞的声音,怎么也睡不着,仿佛有一列车正从我的身体里呼啸穿过。
二
2021年,我四十岁,才写出第二个故事,然后有了第三个,第四个,一直到第七个。
一本书,七个故事,花了三年多时间。久吗?我没觉得。写的时候,什么都顾不上,只是想写,埋着头写。
想象中的故乡与记忆重叠起来,我在笔下重塑了一个新的故乡。
我能看到那片土地上的黄沙、破庙、旧城墙、护城河。老人、孩子、男人、女人,马和骆驼。他们是很渺小的人,是我们父辈那样的人,普普通通地活着,吃饭,喧荒(聊天),相聚,离别,然后默默死去。
当我放下笔,心里又生出疑惑:这年头,有谁还来看这样的小说呢?
2022年12月,在一次写作课后的聚会,我忍不住问何老师,这个时候,还有谁关心一匹马的老故事吗?我们写这些的意义在哪儿呢?
大草老师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说:日本复兴,川端康成作出的贡献,不亚于任何一个大企业。他在穿越废墟的火车上看《源氏物语》,更强烈地意识到,自己要尽可能地写出纯粹的语言,继续倾向于传统主义和古典主义。川端康成的小说给了一代人心理上的慰藉。人们从文学里汲取到的力量是很大的,足以让他们从任何一片废墟上重新站起来。
当时听着很受感动。可下来仍然觉着沮丧。毕竟,我不是川端康成啊!
三
2023年夏天,我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乌鲁木齐。
书里写过的地方,我又走了一遍,边走边拍照。路上的维吾尔族小女孩,卖哈密瓜的哈萨克小伙儿,打馕的大叔。我一直拍。
我们去了二道桥。小女儿在巴扎里穿着维吾尔族人的花裙子,蝴蝶似的飞来飞去,小声尖叫:“妈妈,快拍这个碗!你看多漂亮!”她手里拿着维吾尔族人手工做的一个铜碗,上面刻着细密的花纹。
我在近四十岁的时候,才回头看,那个被我抛在身后的故乡。对我来说,那些过去,从没有如此鲜活,就像这个铜碗一样,闪闪发光。
何大草先生说:小说不是沼泽,不是池塘,而是一条流动的河。
那条河流,就是时间,是我们无法挽回的过去。
这过去,是我的,也是你的。
快离开乌鲁木齐的时候,我一个人去了西大桥,也就是书里的西河坝。那条母亲河已早就看不见了。在我小时候,那儿就建了一座很大的立交桥。
我站在桥上,底下车水马龙,如同一条喧闹的河,奔腾着,向前。
 晋ICP备17002471号-6
晋ICP备17002471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