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直人》中,美国作家理查德·拉索用复古式的幽默语言描写了中年知识分子的婚姻危机和学术混乱,故事涉及的主题和人物群像令人联想到钱钟书的小说《围城》。

图/IC PHOTO
“美国愚人”的写作主题
我们知道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类大多数都是愚人——甚至也包括我们自己,但在文学中“愚人”的体现有太多种方式。幽默与讽刺在这个主题上必然不是最理想的方式,但它一定是最露骨的方式,而且这种方式还能够在表现愚人社会这一主题的同时呈现人性中平凡与温情的部分。这种文风构成了美国早期文学的经典风格,其中马克·吐温可以视为这种文学风格的代表作家。不过这种文风自索尔·贝娄的年代之后便渐渐式微,现在它几乎成为一种怀旧的复古风格,现代读者似乎更倾向于主题尖锐的文学作品,而幽默与讽刺则显得过于温和。理查德·拉索则在当代重拾了这种复古的美国文风,他迄今为止的每一部小说的叙事氛围都极为统一,在幽默的笔调中书写美国社会的“愚人”,描写现代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并在其中书写了普通人那种滑稽又可敬的生活斗争。
理查德·拉索并不是一个有天赋的作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曾经的写作班上,天赋比他卓越的同学比比皆是。理查德·拉索的写作课老师认为,一个人如果想要成为好作家,那就得在写出好作品之前写出1000页糟糕的文字,而如果是拉索的话,那可能得至少写上2000页才行。他从未在写作课上拿过A的成绩,在写作练习上毫不起眼,也没人帮助他出版作品。但在创意写作课程结束的40年后,理查德·拉索是所有人中唯一获得了普利策文学奖的学生。对此,理查德·拉索认为,写作本身是个艰难的过程,“如同人生本身,充满艰辛。而每天,都有许多更加才华横溢的人放弃了这件事情”。他相信音乐评论家马尔科姆·格拉德维尔的“一万小时定律”——即人类需要一万小时的练习才能够让大脑彻底运用天赋。理查德·拉索在写作过程中像他的外祖父一样信奉着工匠精神,他时常会想起自己的祖父加入工匠行会后当了多年学徒才最终打磨出了自己的手艺,而写作同样如此。唯一值得庆幸的是,理查德·拉索尽管认为自己并没有写作天赋,然而他的确拥有着创作幽默讽刺文学所需的首要特质,即一种并不消磨于世界规则中的性格。他在读取博士学位的过程中决定转向文学创作,原因在于他无法接受传统学院研究的束缚。在理查德·拉索的眼中,文学院所从事的工作有些滑稽,特别是在现代,如果一个文学博士要在研究中做出些什么,最佳选择是去研读那些极为冷门的后现代元小说作家,这样才有可能在所谓的学术创新领域写出新的见解,而假如选择麦尔维尔、塞万提斯这些经典作家,则不会获取任何学术成果。讽刺的是,这种文学研究却恰好与文学阅读背道而驰,真正的文学经典在文学研究中反而不被青睐,粗制滥造的元小说作品却会帮助研究者取得极高的文学成就。理查德·拉索就此退出了文学研究,转而开始文学创作。
国内译本将理查德·拉索的小说翻译成“愚人二部曲”,分别是《愚人沙利》《愚人雷默》,但其实它们的英文原名分别是《Nobody’ s Fool》《Everybody’s Fool》,以及还有一本2023年刚刚出版的《Somebody’s Fool》,算是愚人三部曲,分别对应着“没有人是傻瓜”“每个人都是傻瓜”和“我们都是某个人的傻瓜”这三个主题。其中,前两部作品以小镇人物为中心,颇具约翰·欧文的故事风格,讲述小镇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漩涡与苦乐。而2023年的新书被称为三本书中最好的一部。理查德·拉索在美国新冠疫情和弗洛伊德抗议等事件爆发的年份创作了这本小说,在这本小说中,“愚人”不再仅仅是一种日常生活的幽默讽刺,转而具有了一些鲜明的政治意义。书中的当地居民被报纸宣传愚弄,在分裂的政治言论中让自己的生活陷入漩涡,美国文学评论认为这本小说非常契合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后所导致的混乱局面,而这个相关的政治背景,理查德·拉索也在小说中有所体现。
相比之下,拉索一直认为《直人》是他写过的最轻松的小说。这本小说所讽刺的“愚人”对象是大学里的知识分子们。拉索的大学经历以及对文学研究的质疑都帮助他在小说中构建出很多顺理成章的情节。同时,这本小说也讽刺了大学经费和学术机构的僵化。在理查德·拉索上大学的时候,曾经有教授因为无法得到经费而忧心忡忡,那位教授在和拉索于池塘边散步的时候说,“也许我要每天杀一只池塘里的鸭子,他们才会意识到学术经费的必要性。”这只是一句随口的闲聊。但在小说《直人》中,威廉·亨利·德弗罗真的因为学术经费而杀掉了池塘里的鸭子们。
关于中年危机与学术低谷的故事
小说的主人公威廉·亨利·德弗罗在《直人》故事的开篇就遭遇了严重的危机。作者尽可能从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来描写这位大学中年教师的失败之处,包括他已经多年没有更换的旧车,被嘲讽且蔑视的场景,同事泰迪单恋德弗罗的妻子莉莉而形成的微妙关系,以及脸上的伤痕等等。德弗罗破损的鼻子也是拜同事所赐,由于大学决定削减文学院的经费,导致今年只能腾出一个新职位,德弗罗不得不和同事们开会讨论。在《直人》所描述的教授会议中,我们能看到每个人都作为一种标签而发言,有人象征着古典文学精神,有人象征着现代主义,有人象征着女权主义。这些分类让教授之间格格不入,例如坎贝尔·惠默自从研究女性主义之后就留起了马尾,他不能接受任何人仅使用阳性代词,口头禅是说话时补充一句“女性亦然”。而在新职位的研讨会上,给出不同意见的大学教授们也打着各自的算盘,一位名叫格雷茜的教授是目前唯一写作诗歌并教授二十世纪英国文学的人,她想要否定掉某位求职者的原因是她不希望在学院里出现专业与自己重叠的竞争者。格雷茜认为大学里不需要第二位诗人,而德弗罗正是因为嘲讽地发问“那我们的第一位诗人是谁啊”而被格雷茜扔过来的线圈本刺穿了鼻子。
这种混乱而滑稽的场景只是《直人》描写的大学生活中的一幕。回到家中,威廉·亨利·德弗罗还需要处理自己和妻子的感情问题、女儿婚姻的破裂以及自己身体机能的老化。他需要接受自己开始频繁尿失禁的现状——一种文学中非常陈旧的对于男性身体机能衰退的暗示,同时也没有什么比这种事情更能够挫败男性的自信。而在大学里,德弗罗的工作也并不理想,他教授写作课,但课堂上的学生对于文学精神并无太多兴趣,反而更喜欢在写作中大量铺陈类似奸杀场景之类的低俗描写。再加上大学的经费削减,已经身处中年的德弗罗不仅要面对危机,还要面对生活意义的摇摇欲坠。他在池塘旁边散步的时候恰好碰到了来到校园采访的记者,面对记者的问题德弗罗按捺不住情绪的爆发,对着直播镜头高喊如果大学不分配足够的经费的话,他就每天在学校的池塘里杀掉一只鸭子。在小说中,德弗罗真的这么干了。动物保护者站在大学里抗议示威,课堂上德弗罗和学生们的探讨话题从文学变成了“应不应该宰掉鸭子”,完全是一场混乱的哲学场景。“我让他们以论文的形式提交自己的建议,可他们还没来得及把论文交上来,我就显然自顾自地宰了几只大鹅”。顺便一提,小说中的德弗罗教授没有分清鸭子和鹅这两种动物。
英美文学评论对这个场景提出了质疑,因为《直人》这部小说让鹅被无辜屠戮显然不太符合现代的价值观,虽然在文学虚构中这种行为也并无不可,只要它能够从某种意义上为故事主题而服务,但《直人》这部小说也在结局完全忽略了这一点,那些鹅似乎就这样白白死掉了。同时,小说所涉及的对文学教授和文学学生的讽刺性描写,也让作者理查德·拉索忐忑不安,在举行读书会的时候他很担心自己遭遇抗议,但在现场却发现大量来自文学院的读者装扮成小说中德弗罗教授的样子——戴着眼镜和因为鼻子受伤而佩戴的塑料鼻子——对《直人》所讽刺的文学专业表示支持。很明显,理查德·拉索的这部小说运用幽默讽刺的方式,刺穿了存在于大学机构中的虚伪与荒唐之处,也激发了人们对文学研究这种僵化体制的不满。不过作为一部小说,它依旧存在着很多缺陷。也许是受到昔日导师“必须先写出1000页烂文字”的启发,理查德·拉索的每一部小说其实都存在着冗长的毛病,它们的人物与场景过多,故事结构又过于苍白,更像是一集接一集的电视剧而不是一本拥有整体凝聚感的小说。总是匆匆结尾的结局和略显刻意老套的情节转折都让拉索小说的文学价值大打折扣,同时,他在语言方面也有所欠缺。但这并不妨碍理查德·拉索的小说一直受到大量读者的青睐。毕竟,我们并不是永远需要最完美的小说,有时那些能够用引发笑声的方式刺穿某种社会现象的小说,也是我们这个世界所需要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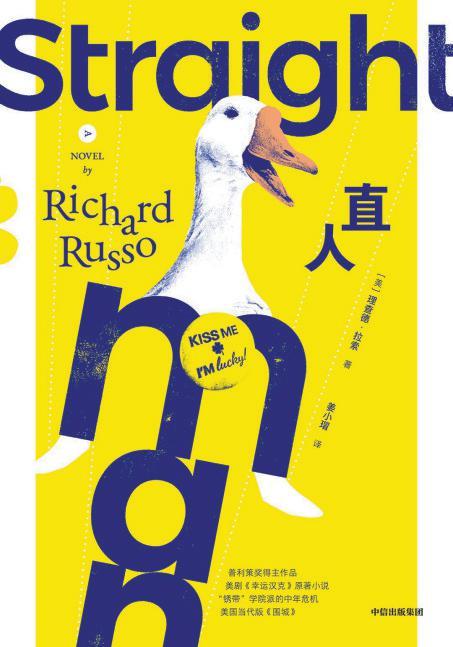
《直人》
作者:(美)理查德·拉索
译者:姜小瑁
版本:大方|中信出版集团 2025年5月
撰文/宫子
编辑/李永博 张婷
校对/薛京宁
 晋ICP备17002471号-6
晋ICP备17002471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