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象·中国当代诗歌巡展(第21期)
本期登场诗人:李点、张光杰、张静雯
亲吻自己
文/李点
那次大醉过后
我在右臂上发现了一处深紫色的吻痕
我问当时在场的女士
她们笑而不语
在场的男士
表现得一个比一个无辜
我无从查证这幸福的出处
怀着一颗好奇之心
我把牙齿涂上口红
在吻痕的一旁轻轻咬了下去
上切牙的突兀
下切牙的扭曲
都别无二致
我有些心碎
醉了的时候,我代替谁
狠狠地,亲吻了自己
(李点,作品见于《诗刊》《星星》《诗潮》《诗选刊》等,入选多种选本。著有合著诗集《草色·番茄·雪》《三色李》。现居北京。)

一个虚无的人
文/张光杰
我在旷野上赶路,前面有一个人
在不紧不慢地走着
我快步追上去
发现他是一团空气
我停下脚步
他又开始向前走去
那熟悉的背影,我好像在梦里见过
现在好了,他们
一个在前面走着,一个在梦里走着
像一对永不碰面的孪生兄弟
我曾经在路边遇到过一个人
那是个古人
他贪睡,一睡就是一万年
醒来,耳朵里塞满了鸡鸣
我向他打听史前的事
他打着哈欠
似乎根本没有听到我在说话
这一次不能错过了
我一定要追上去,拦住他,问问他到底是谁
可他明明就在眼前
却又像从来没有存在过
他就是一团空气
谁也找不到他
但我走路的时候,他又会出现在前方
像我的影子,或者,是明天的我
由于他活在未来
而成了一个虚无的人
(张光杰,洛阳文学院签约作家。诗歌见于《诗刊》《人民日报》《星星》《扬子江诗刊》等报刊。获得首届白居易诗歌奖、2021年度《延河》最受读者欢迎奖诗歌榜二等奖、2020年《青年诗人》十佳新锐诗人。著有诗集《黑咖啡·白咖啡》等。)

最后一个要求
文/张静雯
仅从过去和未来中摄取
就足以悲从心起。我们
不敌时间
灯火璀璨,路灯、车灯
每个窗口的灯,都与星光对峙
黑夜无法躲避,黑夜获胜
石子路颠簸
携一只手表和一面破碎的镜子
我走了——一个未知的未来
和已知的结果
我们到了轻描淡写的年纪
因而从此以后
再也没有遇到类似于你的人
但我还有最后一个卑微的期待。
恳求任何事物不要挡住了
我迎面而来的风
别挡住了,所有我观看的晃动
以及那些不确定的方位
(张静雯,“80后”诗人,出版诗集《未完:365首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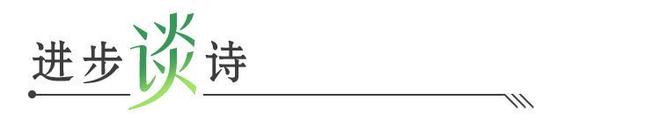
主持人语:
李点这首《亲吻自己》中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是她诗中的“在场的男士”,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才读到这首诗。也因为这首诗,我就在想,我们诗中的“自己”到底是个什么角色?在她的这首诗中,很明显,“我”就是“我”。因为是在场者,我能够证明,这里面并没有虚构或者夸张的成分。但是不是因此,诗中的我,就一定是一个现实中的我呢?
我没有特别明确的答案。
今天还同时推荐了张光杰的《一个虚无的人》和张静雯的《最后一个要求》。这两首诗也都是很明确地在写“我”,但又非常不同。《一个虚无的人》中的我是第三人称的我,或者是他者的我;《最后一个要求》中的我是一个复数的我,或者混沌的我。
其实说这么多,我只是想说:诗是虚构的,诗中的“我”也是如此。如果说小说是虚构的,我们很容易理解;说到诗是虚构的,好像很多人就会停顿一下。但确实如此:诗是虚构的。不但诗是虚构的,一切文学作品都是虚构的。
前面我还说《亲吻自己》这首诗并没有虚构或者夸张的成分,怎么就成了虚构的呢?请看这首诗的最后两句。这两句是好是坏,可能每个人看法不同。但正是这两句,很明确地说明了一个问题,当我们开始写作的时候,我们所写的都是“主观的事物”,在文学中并不存在“客观”这种东西。
张进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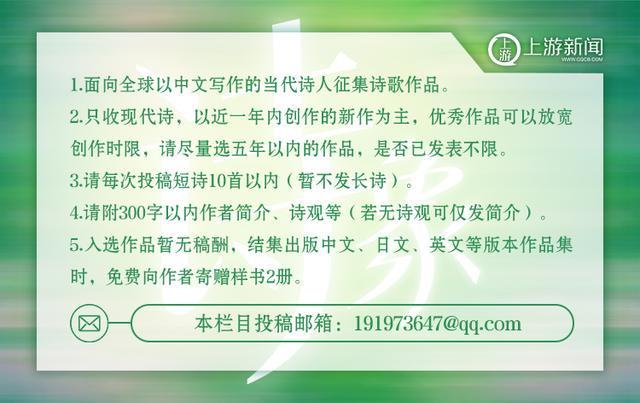
 晋ICP备17002471号-6
晋ICP备17002471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