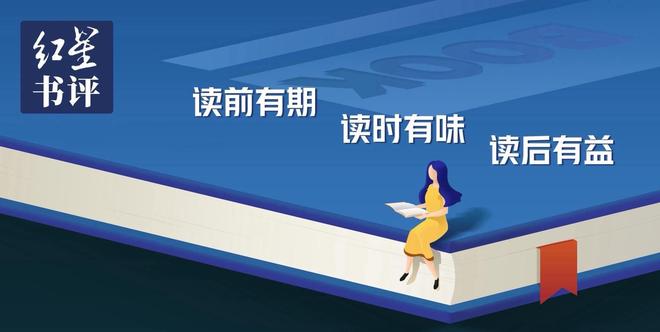
触碰与省思
——庞惊涛散文集《云上》读札
文/杨庆珍
秋日的天空高渺旷远,云朵轻柔变幻,给人无尽的遐想。看云是中国人的赏秋雅事之一。在大地之上、白云之下,静读作家庞惊涛的散文集《云上》,是一种美妙的感受。云朵缠绵,阅读时的心绪也缠绵,头脑里挥之不去两个词:温柔、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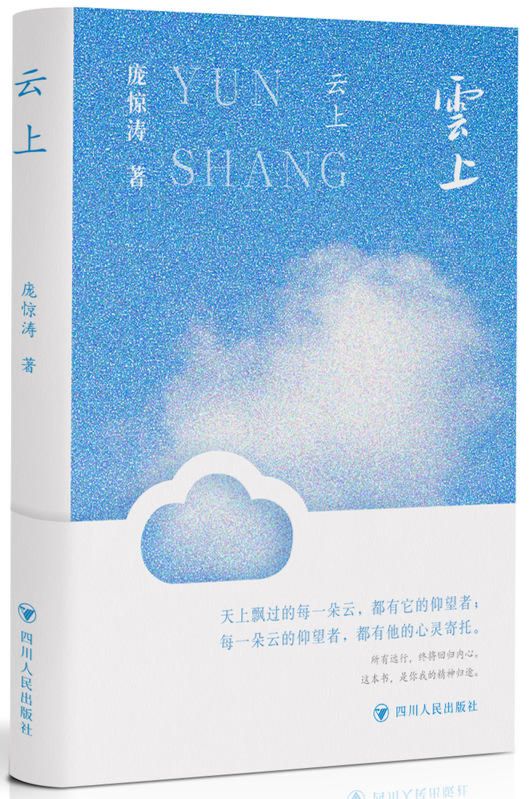
云是温柔的。散文集《云上》以“云”为核心意象,以“云起・故园旧事”“云驻・人间烟火”“云飞・山河远阔”“云归・浮生杂忆”四卷为架构,云起云飞,云驻云归,从山河故园到家族旧事,从红尘烟火到诗心哲思,庞惊涛以十余万字草叶般的文字,以及露珠的晶莹、柴灶的温度、思想的力度,构建起一座血脉贯通、气韵生动、温柔美好的“云上”家园。
这个家园是深情的,有浓厚的烟火气息。《老屋记》中,对乡下老屋一椽一瓦一草一木的深切眷恋;《安仁轻食记》中,对油豆腐、醪糟、绿豆花的生动描写;《花夜》中,一段婚嫁前夜新娘辞别父母的带泪吟唱……其中的亲情与乡愁、牵挂与思念、理解与疼痛,以或打开或折叠的方式,化为一朵朵形态各异、色彩丰富、具有象征意义的云。不过,不同于飘在高空的云,庞惊涛的“云”是可以触碰的,也是可以让人仰望、追忆、省思的。
内容:虚实相生的“云”
云从大地上升起,每一朵云就有了根系。散文集《云上》的根系深深扎入生活,整本书的内容是及物的,书写是沉实的,其中意趣,可谓虚实相生。
先说及物。庞惊涛从一座老屋写起,那些隐于尘烟的人物:石匠明大爷、贺剑叔叔、南池师友……在文字中全都活泼泼地醒来。具象的乡土符号被赋予深层隐喻,活在旧时光里的人,成为昭示生命、承载情感色彩的元素。
细节之处见真章。作者对其笔下的动植物,始终持有一种平等的视角。《牛年六记》中,牛不仅是牛,它不是低于人类的存在,而是独立的鲜活主体,而如何对待牛,昭显的正是人心,他是希望通过记录耕牛的消亡史,传达出每个生命都应该被温柔以待的悲悯意识。

再说沉实。沉浸式的书写,是对乡土记忆细腻、深度的打捞。读者能感受到该书是作家几十年来丰厚生活的积累,其写作素材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亦能感受到篇篇文章功夫扎实,充盈厚重,因为有独立的深邃思考加持,绝无漂浮感。譬如他写《良扇志》,讲述一把扇子如何成为非遗,潮与江、山与竹、纸与墨、技与艺、宫与公,如扇面渐次展开,铺排有序;他写《金川的颜色》,从金、蓝、绿、红、白五个维度展开,既有跳跃感,如春日景象美不胜收,但每个维度均落到实处,恰如金川的古树梨花——它正是五片花瓣,质地厚润,带来甜美的期待。

《寻桂记》中,持续高温,空气里全是燥热的气息,桂园中堂的幽幽灯光下,钧窑梅瓶里斜插一枝仿真丹桂,“我执意要寻找开着的桂花,不是为了让‘花好’来成全‘月圆’,以让良配永不散场,而是借助寻找,消除我们可能会因为极端气候永远失去桂香的某种焦虑和担忧。”莫笑作者痴,字里行间,凸显出他对人与植物相伴相生这一命题的深沉思考。
《庭中有奇树》中,看似平淡的种树,庞惊涛讲述得一波三折,很有情致,“当时我只认这棵存活下来的榆树,是如同我生命存在的奇树”。桃夭过美易夭,榆树因“愚”得以终年。榆树给了作家丰富联想,许是因此,他自号守榆居士,表达出甘为人后的独立、清醒与坚守。作为读者的我,在这里找到了连接的情感纽带。我想到俗语“榆木疙瘩”,意指特别愚笨、死心眼儿、不开窍,每当想起这个榆木疙瘩,好像说的就是我。榆树的意象,成为全书的共情点之一。
内涵与表现的虚实相生,叙述、抒情、议论的交替穿插,使得《云上》一书不落于轻,反而具有沉实的质感。
文风:澄澈雅正的“云”
《云上》的文风有白云般的通透空灵,风格雅正,具有明显的诗性特征。庞惊涛有很高的古典文学修养,也曾在书画金石方面下过功夫,以致他的文字常带轻文言风格,有温润如玉的底色。在碎片化写作、流水式输出、口水诗泛滥的当下,一个写作者能够始终坚守对优雅的汉语言的敬畏与信仰,持续对自己的文字进行锤炼,甚至以近乎苛刻的态度对待自己的输出,这是值得肯定和尊敬的。

这种轻文言的韵味,在《云上》俯拾即是。在《老屋记》中,他写道:
枯檐荣,春雨润,杂花生。一溜已经糟烂的老椽子后面,一树碧翠迎着软嫩慵懒的春光,也迎着我们这几个清明祭祖的归人。目之所及,衰朽老屋,光华粲然,恍然华堂。此时,游蜂纷绕,燕子衔泥,它们的处变不惊里,大约也还有识得旧人的情意。
榆钱一地,清甜扑鼻。在这样的气息里浅睡一场的记忆又一次被激活。上一次隆冬归来,一路依恋,及至看见萧索暗淡的老屋,那依恋便急速消退。这一次却不一样,时逢好春,内心柔软,五感召唤的筹码,是一次强过一次要终焉老屋的强烈意愿。
这些句子显然具有诗歌的质地,凝练、优雅,有节奏和韵律,有画面和意境,不仅有对物象的精准捕捉,更揭示了抒情的本质:表现、传达、投射,在具象与抽象之间跳跃,形成一种独特的张力。

再如《云上白鹭》:
白鹭并非高洁的隐士,为了获得新鲜的美食,它们也不惮那些秽浊的泥脏了它们的双脚和羽衣。
但对于那些带着不怀好意的觊觎乃至攻击、偷袭带来的污浊,哪怕只是一点一滴,它们都会尽快清洗,保持自己的纯洁。
还有,那些强加给它们的“并不高洁”的偏见和误解,它们总是不屑一辩。白鹭用它们一贯不移的品性诠释着“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这句俗谚的真意。
这里,白鹭的洁净与秽浊的泥污形成强烈冲击,视觉感受被转化为空间意象,“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哲思升华为精神遨游。
需要说明的是,篇名《云上白鹭》带着些许道家气质,道可道非常道,花非花雾非雾。他在写住宅区周围的田野、写白鹭,写风景,写生态,核心是想表达自己对现代生态保护的省思。很显然,这种省思意识,使他的散文超越了一般性抒情,进入生态哲学的高度。
观览全书,由于写作对象不同,作家采用的切入角度、表达方式也在随时变换,文字摇曳多姿。私以为,“云”这一意象所指向的变幻不息,其实也在暗示着作者对文学语言的追求:超脱、自由自在,指向不可定格、不受拘束、随物赋形的表达。

情怀:流转延展的“云”
故乡是一个沉重的大词。
从文学的乡土叙事谱系来看,《云上》无疑是唱给故乡的一支恋曲。回不去的是故乡。一个作家曾经说过一句话: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这听起来似乎过于悲观。庞惊涛认为,本质上,“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流转”。流转让“故乡”一词存在着巨大的塑造可能。人需要和沦陷的故乡和解,在不断的地理迁徙中寻求最大的适应度。
从庞惊涛个人的生活履迹来看,这样的“流转”确乎比“沦陷”更客观。他从西充出发,到成都生活后,由东向西,又一路向西,经成华、锦江、青羊、温江,再到大邑,传统意义上的故乡越来越远,新的故乡正在对撞生成。在《云上》一书中,作家既写到故乡西充,也写到阿坝州的金川河谷、青白江的潜溪书院、川西的安仁古镇、眉山的哨楼村、古驿龙泉的东安湖二十四桥……我想他是有意为之,看似不经意,实则深远的安排,足令人震撼和深思,也正暗合了苏轼的“心安之处即是故乡”。可以这么理解,对作者而言,风雨飘摇的乡下老屋固然是故乡的牵系,洋溢着蓬勃生命气息的云上住宅区,何尝又不是故乡?并且,是具有丰盈生命状态的新故乡。这样打量文本,它顿然具有延展性,空间被拓展,时间被拉长,脚之所至、目之所及,都是“云上”。

“天上飘过的每一朵云,都有它的仰望者。 而每一朵云的仰望者,都有他的心灵寄托。”代跋里,庞惊涛如此阐述“云上”的意象。我们都曾“少年心事当拏云”,如今“谁念幽寒坐呜呃”。往事如云烟,感谢庞惊涛,在滚滚时代洪流中,在对精神归宿的深切追寻中,他以文字为丝绳,帮我们拴系住一朵故乡的云。作家道出《云上》的写作初心:以痴情留住昨天,交付明天。如此,往事将永远鲜活,不会如云烟飘散。“我执着于写下旧,是为了让‘你’或者‘你们’知道,曾经有人,这样‘旧’地活过一生。”
如书中所言,“故事不是时间的使者,故事只是时间的证明。证明我们的来处,也证明我们的归途。”读《云上》,最大的收获在于,它让我放缓脚步,放慢节奏,在对云的遥望中,去寻找时间的痕迹,去触摸记忆的肌理、往事的脉络,重建自己的心安之处——故乡。
云朵之下皆故乡。
编辑 苏静 图据图虫创意
 晋ICP备17002471号-6
晋ICP备17002471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