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酒精计划》
“上了飞机我在座位上开始翻阅前面几页,竟然欲罢不能,旅途中一有空就热心地继续读下去。我已经好久没这样忘我入迷地读一本小说了。”
在挪威奥斯陆旅居之时,村上春树偶然被书店中一本“书名实在很怪的”的书所吸引。他买下了它,一口气读完了它,甚至打破间接翻译的原则,将它译介给更多的日本读者。
这本书便是达格·索尔斯塔的《第11部小说,第18本书》。这是村上春树第一次阅读索尔斯塔的书,很快就被其“毫不动摇的独创性”所折服。
达格·索尔斯塔便是这样一位具有魔法般吸引力的作者。无数作家喜欢他——美国作家莉迪雅·戴维斯为了能直接阅读索尔斯塔作品原文,决定搬到北欧学习挪威语;挪威著名小说家佩尔·帕特森誉他为“挪威最具勇气和智慧的小说家”;挪威评论家阿内·法赛塔斯则在《巴黎评论》的文章中称索尔斯塔为“挪威最伟大的在世作家” (已于今年逝世) 。不过,的确,他是唯一三次获得挪威最高文学奖项文学评论家奖的作家。
一份无意义而必须维持的工作、一个始终无法融入的环境、因惯性而延续的生活轨迹……《第11部小说,第18本书》和《安德森教授的夜晚》,两本真正的存在主义小说,它们捕捉到这些我们都习以为常、又想从中挣脱的处境,共同展现了索尔斯塔的独特魅力——以冷峻、优雅的语言,打破了我们日常生活安宁的表象,揭示其中暗藏的虚无、荒诞、孤独、不安,以接近喜剧的方式,道出人类生命中最深刻的困境。
《第11部小说,第18本书》
译后记(节选)
奥斯陆是个相当漂亮的城市。搭乘路面电车可以很方便地到达任何地方,想散步的话,步行距离很刚好,即使住上一个月也丝毫不感厌倦。这里既是挪威的首都,又是最大的都市,但人口并不太多,市容清洁治安良好。8月既凉快又舒适,夜晚甚至还有点冷。然而停留长达一个月之久后,带来读的书果然不够了,因此我到瑞典小旅行时,就在奥斯陆机场的书店找英文书。就在那里偶然看见这本达格·索尔斯塔(Dag Solstad)的《第11部小说,第18本书》,一本书名实在很怪的小说(原名是Ellevte Roman, Bok Atten,意思是对他来说的第十一本小说,第十八本作品。是什么就说什么,非常直接的说法)。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谁是索尔斯塔先生,不过因为是挪威作家的英译本,很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小说,就把书买下来。当然多少也是被那样的书名吸引。
上了飞机我在座位上开始翻阅前面几页,竟然欲罢不能,旅途中一有空就热心地继续读下去。我已经好久没这样忘我入迷地读一本小说了。
总之是一本不可思议的小说,这是我读完后合上书,毫不虚假的感想。不仅书名独特,内容也独具风格与众不同。甚至可以说,好在哪里我也说不太清楚。虽然如此,但总之很有趣。一边读心里一边想“这故事到底会变成怎样呢?”一边凝神屏息地读到最后。不过,说真的,这真是满古怪的故事。
要问怎么个怪法,首先是那小说的风格。到底是新还是旧?连这个我都难以判断。文体和情节猛一看似乎相当保守,但整体呈现的模样绝对是前卫的。每次有人问我这本书“到底是什么样的小说?”我都暂且以“这个嘛,可以说是披着保守外衣的后现代作品……”回复,因为除了这样的答复,我也一直想不到更适当的说法。后来我还浏览了索尔斯塔先生的其他作品,发现这似乎就是他小说特有的风格。
手法上虽然就是彻底的写实,但在那写实之中却又有着微妙脱离现实的地方……总之,他的写法和时代的流向或风尚,或文坛地位之类的都无关,完全是要彻底追求自己的个人风格,他似乎就是属于这个类型的作家。
他的风格,和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现代作家都不像,非常独创。我之所以会在读了这本书之后被如此强烈地吸引,原因我想就是他那毫不动摇的独创性。

《寂静人生》
总之,索尔斯塔的文体相当特异,故事始终以理性推演发展下去。而且他几乎都是以极短的文句和极长的文句交互出现。短文章就如雷蒙德·卡佛般简洁直率,长文章的逻辑则感觉仿佛像“盒中盒中盒”般,装填得密密实实的。要把那一层层分解剥开,转换成日语的文章实在相当困难。如果照样翻译的话会变成不是正常的日语(因为日语并不那么合乎逻辑),因此必须仔细地分别解剖,有必要适度分节,重新排列组合,才容易了解。此外他的原稿几乎不太换行,文章不分段落章节地写下去,如果照那样的排版印刷,书会变成满页黑压压的。欧洲语和日本语,一眼看上去黑的感觉相当不同,我考虑到阅读时的易读性,翻译时换行不得不比原文稍微加多,这点希望读者谅解。
其次,他的文章几乎看不到所谓心理分析这东西。当然并不是完全没有,不过写到了就写,可能唐突地结束,极度缺乏“因此怎么样”的故事发展逻辑。虽然会描述当时的心理,但读完却对来龙去脉不明确,既不知道来历,也不清楚去向。至少那些文字完全不是说明性的。对读者可以说是一种超现实的“放任不管”的感觉。
我一边感觉好奇怪,读完这本书之后,又一边把小说中重要的预备道具、很久没读的易卜生的《野鸭》重新拿起来读,竟发现这本小说跟《野鸭》之间有相当根柢相通的氛围,非常惊讶。两本书中所飘散的空气非常相似,《野鸭》中的出场人物虽然分别有着不同的背景,各自怀着不同的意图生存着,从我们现代的眼光看来(我想象从当时人们的眼光看来,可能也一样),全都是有点奇怪的人。他们的心理和意图在剧本中大致都有了说明,也可以理解,但读者却几乎不可能对他们产生移情作用。为什么呢?因为对那些人的心理和意图,即便各自都有个人的道理,但那些道理之间并没有彼此产生有机的结合。那些彼此擦肩错过或互相碰撞之后,唯有迷失去向而已。而且在这层意义上,出场人物看来多少都显得有点偏执、古怪。
而且正因如此,最后终究会遭遇大悲剧。那种擦肩错过的方式,彼此碰撞的方式,在易卜生的戏剧中,和索尔斯塔的小说中,真是令人惊异地相通。说得极端一点,在他们两人的作品中出现的人们,似乎都在刻意避免彼此了解。
这种“作风”是挪威文艺特有的吗?或只是易卜生和索尔斯塔两人之间特有的共通点呢?我不知道。不过,我想读者可以像肤触般感觉得到,由于那里风土的严酷,和人心所处的某种窘困,使得他们虽然如此,依然(或者应该说正因如此所以更加)不得不追求伦理观或道德意识之类的东西。而作者透过那独特灵巧的幽默感(那只在细部极轻微地不断渗出),和虽然压抑却巧妙的说故事手法,非常高明地将那痛切缓和下来。那适度的调和真是美妙,令我感动佩服。

《寂静人生》
《安德森教授的夜晚》
译后记(节选)
两年前应出版社的邀约,我接下了翻译索尔斯塔的《羞涩与尊严》和《安德森教授的夜晚》这两本书的工作,缘由之一是我对曾允诺要译的一本书最终未能兑现心中怀有的几分歉疚,第二,或许也是更重要的原因,这两本书的篇幅都不长,应该费时不多。但当我真正坐下来开始逐字逐句翻译时,才额上泌出汗珠,感到是自己大大的误判。
1965年达格·索尔斯塔发表了他的处女作,一部短篇小说集《螺旋》。1990年代是索尔斯塔的创作高峰期,他的三部具有影响力的小说《第11本小说,第18本书》《羞涩与尊严》和《安德森教授的夜晚》都出自这个时期,并且它们出版的时间相距都不过两年。索尔斯塔的作品在挪威和国际文坛上获奖无数,被翻译成近四十种语言,他被誉为挪威当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所以这里我应当感谢出版社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挑战自己,做一次新的尝试。
对平日只读过几本闲书的我来说,索尔斯塔的语言风格是十分陌生的。文中句式繁杂,层层叠叠,有许多的插入语和从句,一不留神便会“误入歧途”,或被弄得眼花缭乱。记得书中使用的一个括弧,包含有长达近一页的内容。但为保持原著的风格,我保留原文的分段,保留它们松散的长句形式。书不厚,但词汇的信息量大,加上有好些字典上无从查找的习惯用语,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不免有许多困惑和烦恼。
小说里的人物在他们心里独自徘徊,我在书页的字里行间爬行相伴。待那些繁杂的段落走下来,渐渐体会出其中的机智与奥妙时,那柳暗花明的美妙我便独享了。
两本书的主人公,这两个各怀心事的中年男人(一个高中教师和一个大学教授),他们似乎有好些相同之处,生活优渥,思想成熟,性格孤僻,前者有点酗酒的毛病,后者也是个好杯之人,对自己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现状他们都感到深深的不适应。不知怎么,这两人让我立刻联想到《局外人》里的默尔斯。大概是因这三人的共性:他们对这个社会始终有一种无法排遣的疏离感,他们完全不以大众的评判标准来看待社会上的人与事。

《心房客》
不同之点仅在于默尔斯坚持自己的原则,他直接、公开地表示他和这个社会的不合作、不和解,而这里的两位却一直深深陷于自我的纠结中,在两种意识里徘徊不定,内心的探索、思考、评判对他们一直紧追不舍,甚至到了近似疯癫的状态。
下面再说说这两个故事。高中老师茹克拉,一天在挪威语课堂上,诸多不顺心让他感到挫败,以至于下课后他因为打不开一把雨伞,在校园里恼羞成怒;安德森教授在平安夜,从公寓的窗口目睹了一起谋杀案,于是他一直纠结在是否应向警方报案的问题上,但最终他却并未采取行动。两个看似荒诞的故事,人物行为的莫名其妙,说话的喋喋不休,语无伦次,但却让你能耐心地读下去,盼望看到故事的结局。同时他们也给你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既熟悉又陌生,在你的生活里似乎就有过这样的人。
简单又复杂。几句话就可以讲完的故事是简单,但全书贯穿自始至终的大段涉及文学、历史、哲学、宗教等多方领域的思考和评论,要理解并重述它们就不太容易了。我们不知索尔斯塔本人是如何考量的,且让我做一个大胆的猜想:作者在这里或许仅是以故事的走向作为手段,在穿针引线,而他真正的用意是为阐述和表达自己心里的某些观念?从他的社会背景来看,这个设想似乎也并非没有可能性。索尔斯塔曾当过教师,曾就读于奥斯陆大学,很早就进入了激进期刊的文化圈子,1970年代参加了挪威工人共产党(AKP)。他是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他的小说政治色彩浓厚具有反思性,我觉得他的心里一定有许多话想说出来。
当然这两本书看下来我也明白了,不管话题如何天马行空,索尔斯塔最后都能自然地回到原点,沿中心线继续往下走,直到他要思考或议论的话题出现,然后一个一个地继续下去。突兀但也自然,无可理喻又可理喻,烦恼又迷人,这就是索尔斯塔文字风格的特色与魅力,最终他会让你慢慢地接受故事里的这个角色,并且相信他的存在,因为那种情绪的感染实在太深切,太令人难以抗拒。
“挪威最勇敢、最聪明的小说家”
“一位讽刺作家,一位喜剧作家,一位实验作家”
“揭示了人类关系的所有喜剧性痛苦”
“准确地指出了生活中引发灾难的那些微小时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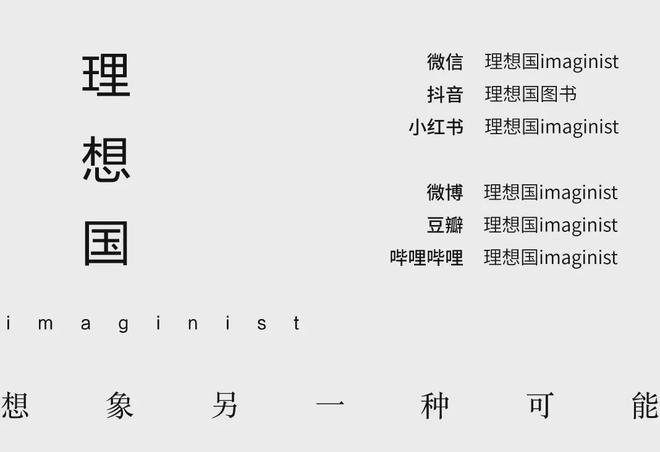
 晋ICP备17002471号-6
晋ICP备17002471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