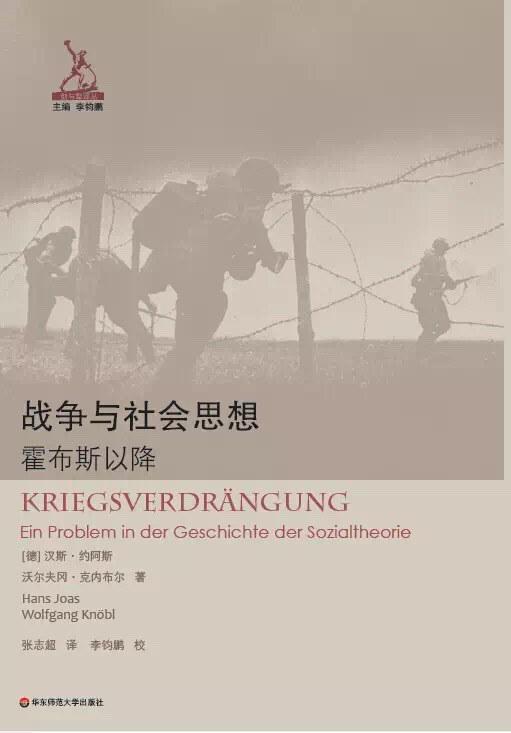
《战争与社会思想:霍布斯以降》,[德]汉斯·约阿斯、沃尔夫冈·克内布尔著,张志超译,李钧鹏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360页,68.00元
一
战争既是一个古老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古老的社会理论问题。在有史可考的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对战争的理论反思可以上溯至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甚至,柏拉图的《理想国》也包含了对战争的系统思考。柏拉图通过战争来分析人的灵魂结构,认为战争植根于人们竞逐荣誉的意气(spiritness)。他将战争视为公民教育(音乐教育与体育教育)的前提,也把战争当作理解理想政体的枢轴。在《战争与社会思想》这部著作中,汉斯·约阿斯(Hans Joas)与沃尔夫冈·克内布尔(Wolfgang Knöbl)致力于重建战争的社会理论史。不过,他们的理论重建带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无意不加裁剪地重述从古至今的战争理论。
两位作者在著作开篇就揭示了社会学的理论困境。尽管二十世纪是“战争的世纪”,但是,“只要一瞥1945年之后的社会学(从那时以来,它就一直声称社会理论这一领域主要或专门由其统辖),我们就会注意到暴力和战争对其产生的影响是多么地微乎其微”(第1页)。二战结束后,塔尔科特·帕森斯、于尔根·哈贝马斯、尼古拉斯·卢曼、皮埃尔·布迪厄等学者跻身“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行列。在他们的人生经历中,“战争无疑扮演着创造性的角色”(同前)。但是,在其著述中,除了雷蒙·阿隆,他们都没有把战争及其相关现象当成一个严肃的问题来看待。绝大多数理论家“几乎总是完全或远远地绕开战争现象”,哪怕他们试图为“现代性”提出一种系统性的解释。在他们眼中,现代社会仿佛“没有经历过一再反复且大规模的国家间暴力的阶段”,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也好似一个“线性的分化和理性化进程”,社会变迁则被认为“总是和平的甚至和谐的进步”(第2页)。总而言之,当下的社会学(尤其是社会理论)对战争现象甚至更一般的暴力现象视而不见。约阿斯与克内布尔忍不住发问:这究竟是为什么?
在他们看来,当下的社会理论特别缺乏历史视野,以致罔顾战争、暴力等社会事实,表现出理论上的昏盲与无知。所以,他们试图以战争为线索,对社会理论作一番历史的考察,梳理社会理论的演化趋势,透视其“变形”及因由,以期恢复社会理论的清明与活力。“我们在本书中侧重考察战争与和平方面的社会理论史。我们关注的时段始于近代托马斯·霍布斯的研究引发的关注政治现实的思想革命,迄于当下。”(第1页)关于霍布斯带来的“思想革命”,约阿斯与克内布尔不惜笔墨,写下很长一段论述:
与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不同,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断然与古典自然法理论划清了界限,并将其哲学和政治理论建立在严格的个人主义假设之上。斯多葛学派和经院哲学的自然法理论全都假定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由法来统辖的,嵌入其中的个体能够认识而且也必须遵循这些法则。霍布斯则摆脱了这种成见,只承认个体的自我保存权利为唯一的自然权利。诚然,在他的理论框架里几乎没有上帝的位置;但对于社会理论上的探讨而言,更为重要的却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他由于抛弃了经典自然法理论关于人类自然社会性(Geselligkeit)的习惯说法,便不得不基于人们彼此之间漠不关心的人类学假设,从个体自私的利益追逐中推导出了社会的秩序。霍布斯把人类的行为能力化约为激情和利益的实现,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自然状态的设定应该能够以近乎几何学的方法证明,那些被描述为自私自利的个体怎么能和为什么能就普遍认可的秩序达成共识。(19页)
论及霍布斯带来的“思想革命”,他们的观点可谓“卑之无甚高论”,只不过沿袭了政治思想史“剑桥学派”的论断。剑桥学派认为,霍布斯奠定了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约阿斯与克内布尔将战争社会理论史的起点追溯至霍布斯,这一做法只是“遵循哲学和社会科学中的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第1页)。而且,这一传统在“列奥·施特劳斯和塔尔科特·帕森斯等人著述中都有鲜明的体现”(同前)。这一思想传统认为,霍布斯开创了一种理解政治与社会秩序的现代方式,即所谓的“个人主义假设”。霍布斯拒绝了古典自然法理论关于支配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先验法律的观点,致力于从普通人的人性中找到摆脱自然状态、消解冲突、缔结政治社会的基础与法则。所以,约阿斯与克内布尔强调,社会理论以霍布斯的《利维坦》为开端(18页)。因为,社会理论在此找到了“继续前进的出发点”,或被抨击的“靶子”。这时,他们就强调了社会理论与现代性之间的内在关联。由于霍布斯完全抛弃了古典自然法理论“关于人类自然社会性(Geselligkeit)的习惯说法”,十分激进地将人类的自然状态设定为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状态,他的学说就引发了众多批评,开启了关于人性、和平与秩序的争论,并在十六至十八世纪孕育出一些“替代性的和平构想”(22页),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社会学的理论先驱。
不过,约阿斯与克内布尔将社会理论的开端追溯至霍布斯的《利维坦》,这一做法违背了社会学学科史的通常论断。“社会学的学科史通常以该专业的古典作家从而也就是以十九世纪为开端,而把更早一些的学者当成不成熟先驱来处理。”(11页)对于社会学的学科史而言,他们围绕战争问题展开的对社会理论史的重建就具有了某种“反传统”与“反潮流”的意味,并因此展露其批判意图。倘若为社会学界普遍接受的学科史没有缺陷,他们为何还要多此一举,着力重建新的社会理论史呢?
按照既有的学科史叙事,社会学降生于十九世纪。与此同时,十九世纪也是“自由主义的世纪”(同前),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无疑接受了自由主义的洗礼。这或许是当下社会理论对战争问题视而不见的原因。“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理论方面的各种思潮深受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基本假设的强烈影响,总是对暴力现象视而不见。”(第5页)所以,为了“推动学科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为“建构经验上有说服力的社会学理论和现代性理论提供一些线索”,我们就有必要摆脱自由主义偏见造成的思想遮蔽,将学科史延展到自由主义时代之前,在自由主义的框架之外寻找思想刺激与理论启示。
在著作的结语中,两位作者直接地表明心迹:这本书可以说是一本与功能主义思想暗中较量的论战之作——功能主义思想并不只是存在于以“功能主义”概念自称的著作里(294页)。两位作者曾经合著《社会理论二十讲》,在这部著作中,他们梳理了功能主义社会理论在二十世纪的流变:帕森斯如何集各家大成,发展出功能主义的社会系统理论,进而影响哈贝马斯、卢曼等一众社会理论大家,以及后来的“现代化理论”(参见[德]汉斯·约阿斯、沃尔夫冈·克诺伯:《社会理论二十讲》,郑作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在他们笔下,帕森斯开创的功能主义理论传统留下了非常明显的自由主义烙印。他们明确批评帕森斯的进步史观,这种单一线性的进步史观无疑是自由主义的遗产。“帕森斯提出的汇聚命题最值得批评之处,就在于他的汇聚命题是一个相对单一线性的进步史观……帕森斯自己却也以信奉进步的态度来阐述思想史。这是他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中的一个矛盾,而他自己却没有看到。由于帕森斯的阐述实际上是信奉进步的,所以言语之间都透露着这样一种信念,即认为有一条清晰可见的从古典社会学家通向帕森斯自己的进步道路。”(同前,49页)再者,在帕森斯的社会系统理论中,功能分化的基础是社会持存。“一个社会系统,会以它自身内在所拥有的资源,来满足长期持存所需的一切本质方面的、功能方面的先决条件;这种社会系统被我们称作社会。‘社会’这个概念并不是说,社会在经验上无论如何都不应该与其他社会相互依赖,而仅是说社会应该包含一个独立持存的系统所要具备的结构基础和功能基础。”(同前,63页)社会持存观念背后则是一套和谐、平衡的秩序假说,从而遮蔽社会中的冲突与战争,导致帕森斯的“宏大理论”与经验现实“危险地脱钩”(同前,142页)。就其思想底色而言,帕森斯关于社会持存的功能主义分析也具有明显的自由主义色彩。在重建战争的社会理论史时,约阿斯与克内布尔也构建了一个思想的战场。实际上,他们与功能主义的较量亦可归结为他们与自由主义思想传统的论战。他们之所以突破既有的社会学学科史叙事,将战争的社会理论史开端追溯至霍布斯,原因就在于他们对自由主义传统的不满,并试图对十九世纪以来的自由主义理论传统发起挑战与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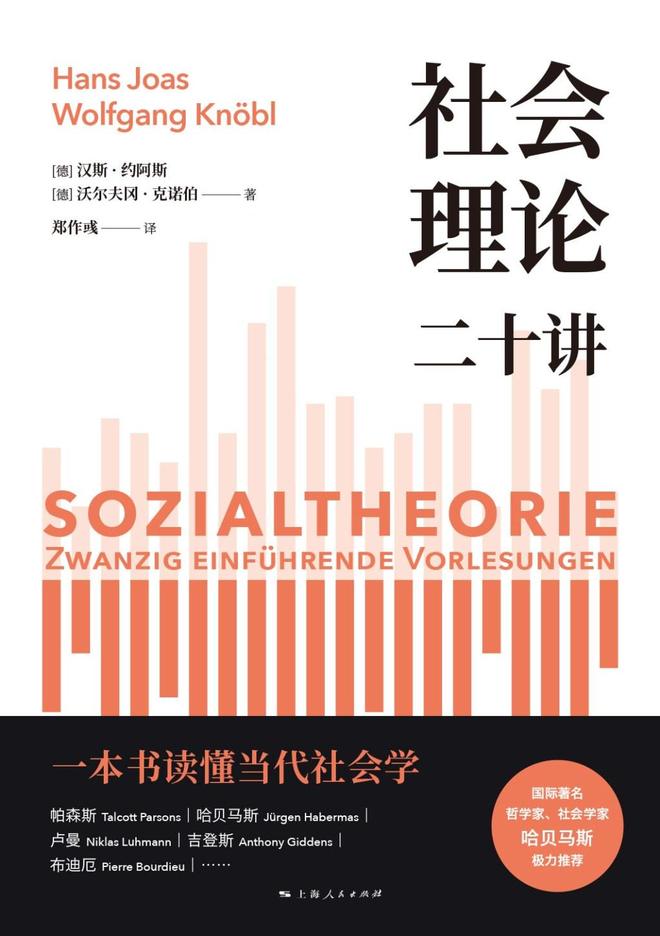
汉斯·约阿斯与沃尔夫冈·克内布尔合著的《社会理论二十讲》
二
与既有的学科史相比,约阿斯与克内布尔尤为关注“战争社会理论的早期史”。亦即,他们特别关注那场发生在十六至十八世纪之间,由霍布斯开启的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想论争。为此,在阐述经典社会学家的学说前,他们专辟一章讨论“社会学诞生前的战争与和平”(即第二章:社会学诞生前的战争与和平:从托马斯·霍布斯到拿破仑战争)。这是自由主义的前史。通过梳理发生在自由主义时代之前的思想争论,他们希冀打捞起那些“被自由主义强化、忽略和排挤到边缘”的思想(11页)。他们也力图揭示:在自由主义取得胜利之前,启蒙运动时代的思想图谱斑斓多元,思想家们围绕战争与和平问题展开了众声喧哗的,乃至相互冲突的论辩,从而更完整、更丰满也更真实地呈现出社会事实。
启蒙运动时代也是欧洲国家间体系的大转型时代。在十六至十八世纪这一时期,神圣罗马帝国走向瓦解,绝对主义国家兴起,现代国际关系体系逐渐成形。也正是在这一阶段,众多思想家围绕战争与和平问题展开了系统的思考,并对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产生重要影响。约阿斯与克内布尔援引英国政治学家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的论述,区分出三个相互竞争的思想传统:霍布斯主义或强权现实主义传统、格劳秀斯主义或国际主义传统,以及康德主义或普遍主义传统(18页)。在政治思想光谱中,关于国际关系的理解,这三个传统分别位于永恒的战争、国际社会中的战争与和平,以及永久和平三个区间。这三个区间当然构成了一个连续且完整的谱系。然而,这仍然是一个过于简单的描述,无法呈现思想争论背后的现实关切与细微差异。
约阿斯与克内布尔将启蒙运动时代的战争社会理论区分为两部分:霍布斯的强权现实主义学说,以及后世学者提出的替代性和平构想。按照这一结构,他们分别阐述了霍布斯、孟德斯鸠、苏格兰启蒙学派(弗格森、休谟、斯密、米勒)、边沁、卢梭、康德,以及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的思考。他们的思想阐释既要凸显众思想家在主题与逻辑上的承继与呼应(在某种意义上,批判也是一种承继与呼应),也强调他们各自面对的历史情境。于是,在他们笔下,启蒙时代的战争论述既有其连续性,又有诸多转折与断裂:
尽管霍布斯抛出了一连串关于和平的问题,留待后来的思想家回答,但是他们给出的答案却并不总是切中霍布斯的问题,在社会历史语境不断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尤其是这样。不过,我们可以认为,霍布斯为后来的一些讨论勾画了轮廓,这些讨论主要围绕着人类行为能力的人类学问题,臣民与国家首领之间的关系形态(这直接影响到供国家差遣的军事权力机器)以及与此相关的国家间秩序的殊性问题而展开。不过,也出现了一些出乎霍布斯意料之外的新问题,以致十八世纪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社会理论在保持连续性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断裂。(23页)
在某种意义上,约阿斯与克内布尔对思想人物的选择也呼应了布尔提出的三个思想流派:霍布斯代表了强权现实主义;孟德斯鸠、苏格兰启蒙学派呼应了国际主义传统,从公民人文主义角度深入反思了战争、商业与德性诸问题;边沁、卢梭、康德则围绕永久和平这一普遍主义问题展开讨论。克劳塞维茨第一次尝试“真正系统地界定战争”,向“启蒙时代的和平构想”挥手作别(74-75页)。对两位作者而言,克劳塞维茨是一个集大成者,对启蒙时代的战争与和平争论做了最终的总结。在这一章的论述中,约阿斯与克内布尔着重强调了商业对公民人文主义传统带来的挑战,凸显了思想家们围绕“贸易和平论”展开的争辩。所以,这一时期的战争论述呈现出足够广泛的理论视野,既涉及政体、道德,也涉及经济与贸易。关于启蒙时代的战争论述,他们总结为三大主题:
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和平政策争论主要围绕三个主题进行:超越国家秩序或国际秩序的形式,其重点是国家内部宪制与对外政策的辩证关系;市场促进和平的潜在效果;民兵理想的重要意义,这里重点关注的是国家与其臣民的关系。虽然我们也没有忽略其他的一些方面,如战争的正当性问题,帝国主义与战争的联系问题等等,但是这些也都包含在上面所说的三个主题之中了。(77页)
十六至十八世纪期间的战争论述必须应对全新的历史情境与思想革命。但是,古典政治伦理(公民人文主义理想)仍然维持着精神上的连续性,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人们对战争问题的理解与思考。所以,与十九世纪之后的学科史相比,十六至十八世纪期间的战争论述从诸多维度调用理论资源,各种思想传统相互激荡,精彩纷呈。战争的本质与道德基础,战争与国家和经济秩序的关系就在这思想激荡中展开、呈现。与之相比,十九世纪之后的战争社会理论则遭遇“变形”,受到社会学学科意识的规训,显得更加单调与空泛。“我们将会看到,十九世纪的和平政策争论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些基本立场(和主题)大体上要比其他那些更受关注,有些甚至整个地销声匿迹并被新的一些所取代。这并不全是因为这些理论接近现实的程度各有差异,而常常是偶然的机缘所致,而其影响也波及今天的社会理论。”(78页)
三
在约阿斯与克内布尔笔下,自启蒙时代以来,经过十九世纪,再延伸到二十世纪的战争社会理论史呈现为一部逐渐下行、日趋单调和干瘪的思想史。以至于,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关于如何缔造和平的结构与过程,社会理论也没有产生令人信服的成果。尽管社会理论家采取的进路互不相同,但它们都“只关注单一主题和单一因素”。他们在讨论战争及可能的休战时,也总是只被“某一种宏观社会学过程牵引”(291页)。他们强调,战争社会理论之所以呈现此等历史轨迹,陷入此等失败困境,十九世纪的漫长和平是一个关键环节(1815至1914年这近百年时间里,欧洲享受了漫长的和平与繁荣,因此,约阿斯与克内布尔将第三章命名为“十九世纪的长期和平与社会学的诞生”)。在十九世纪孕育成熟的自由主义思想最终捕获了战争议题,放大了永久和平的普遍主义立场。社会学便诞生在这样一种思想环境下。尽管自由主义和评论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惊人的“迂回”,但它仍在社会理论中成为一种主导性的意识形态。“人们常把十九世纪称作自由的世纪。这当然有充足的理由。毫无疑义的是,这种自由主义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形式,它也开始把迅速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视为自己的对手。不过,这一与之对立的思潮也分享了不少自由主义的假设。”(79页)结果就是:“十九世纪,曾有很多社会学家和社会理论家幻想没有暴力的现代性,而这个迷蒙也只是被短暂地打破而已。在一战过后,这种迷梦依旧不灭,而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只有极少数的学者让各自的学科短暂地记起了战争的现实性。”(184页)
很明显,约阿斯与克内布尔的思想史叙事挑战了帕森斯的“单一线性的进步史观”。在关于战争的思考中,这段思想史的起点反而最是精彩纷呈。“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我们的写作中,恰恰是那个据说对进步极为着迷的启蒙运动时代的例子极为有力地证明了,社会理论处理战争现象的历史不能被写成一部进步史。”(12页)于是,过去与历史就构成了对当下与现实的批判。他们也借以重申思想史的价值。他们拒绝认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过去是“一个堆满过时观念的垃圾场”(同前)。相反,他们强调,“不只对于历史学家,而且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也是,回顾思想史是很重要、很值得做的事,因为人们永远都可以从中发现新东西。”(《社会理论二十讲》,49页)
约阿斯与克内布尔响应厄恩斯特·卡西尔的号召,主张严肃对待启蒙哲学中的内在冲突,深刻思考社会理论史上的争论,从而彻底抛弃当前的“单主题进路”(291页)。所以,他们不仅致力于重建战争的社会理论史,也呼吁当今学人重建社会理论。以此批判的社会理论史为鉴,他们发现,迪特尔·森哈斯(Dieter Senghaaas)的“文明六边形”构想就是战争社会理论重建的典范。森哈斯之所以能够突破“单一主题单一因素”,其紧要之处在于:“森哈斯的分析方法从过去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争论中汲取了教训。”(293页)所以,思想史是一种批判的、自我反思的方法;历史中的思想则有可能是富含智慧的宝矿。
 晋ICP备17002471号-6
晋ICP备17002471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