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由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浙江省作家协会与阅文集团主办的郭羽、溢青《面纱》作品研讨会在线上召开。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弘,浙江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叶彤,阅文集团副总编辑田志国,专家、评论家白烨、欧阳友权、周志雄、夏烈、乌兰其木格、程天翔、涂国文、汤俏、周敏、战玉冰、谌幸,责编陈悦桐等,共20余人参加研讨会。会议由何弘主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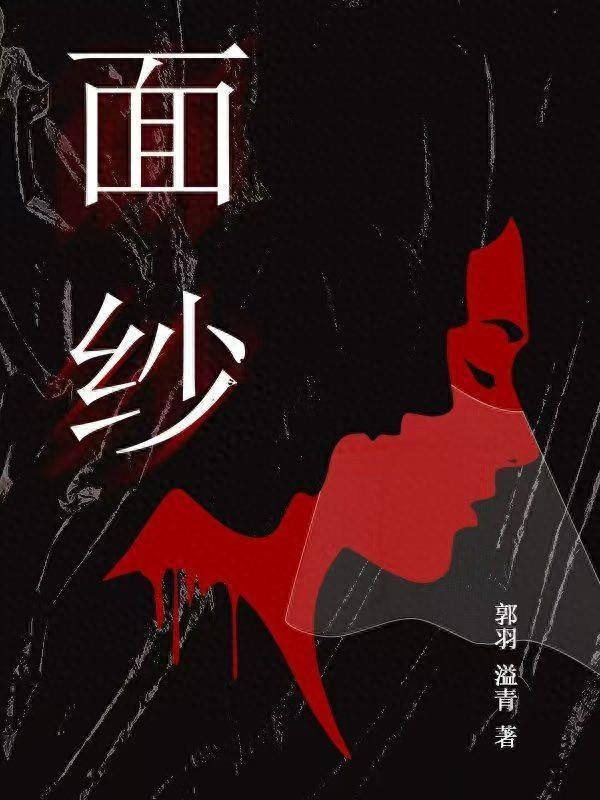
何弘指出,近两年,网络文学正从过去偏重幻想与爽感的凌空蹈虚创作,转向对现实社会的深度介入,开始讨论人的经验与社会问题,这种变化不仅是题材的拓展,更是文学自觉的提升。《面纱》以悬疑类型为外壳,直指网络暴力这一时代病灶:通过女主角黎敏被诬陷、遭遇“社会性死亡”、最终整容复仇的悲剧链,展现网络舆论对人产生的深重伤害,这种书写实际上触及了网络时代社会治理的深层困境。更值得关注的是,作品将“社会性死亡”现象提升至人的存在本质的探讨高度:当一个人的社会身份被彻底剥夺,其精神性存在是否就此消亡?《面纱》以文学的方式回应了“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哲学命题,它揭示人不仅是生物性存在,更是精神性存在,这种对人性困境的洞察,使作品具备了超越类型小说的思想重量。
叶彤表示,《面纱》具有悬疑小说好看好读的特点,又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多线条交织的叙事手法逐步推进情节,揭示网络舆论场如何演变为舆论的审判庭,舆论的巨浪如何逐渐偏差,从而淹没个体酿成悲剧。文本并未停留在对“网络暴力”现象的简单描摹,而是通过小说主角出人意料的“复仇”设置,将作品引向了更深的哲学层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当下媒介伦理、身份焦虑与正义困境的文学样本。
田志国认为,书中没有非黑即白的角色,多维度的人物刻画,让读者不断追问:谁才是真正的凶手?作为一部现实悬疑题材作品,《面纱》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无需依赖血腥暴力,而是以无形的人性压迫为“凶器”,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社会观察,直击现实痛点。这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笔法,恰恰体现了作者对现实题材的深刻把握。
与会专家高度评价《面纱》是一部非常成熟的社会派悬疑小说,是一部富有现实关怀、人性关怀、叙事水平的作品,对标日本、欧美的同类型畅销书,不遑多让。小说以身份错位与层层反转的叙事结构构建其悬疑张力,在情节架构上融入了1998年洪灾、网络暴力、冒名顶替、性别歧视等多重社会议题,展现出对现实困境的强烈关注和文学表达的野心。
与会专家指出,小说既具有类型文学的“强情节”和故事性,同时又以敏锐的观察揭示出媒介变革时代的社会病象和社会热点议题,从而在通俗叙事中完成了对人性与社会的勘探与叩问,突破了类型化写作的桎梏。在技术加速迭代的当下,小说烛照的不仅是一桩令人感慨的罪案悲剧,更呈现出我们共同面临的伦理困境与技术赋权下的人性异化。


研讨会上,郭羽、溢青分享了《面纱》的创作历程。小说里,他们选择把网络暴力这一社会议题和三位经历了1998年洪灾的女性命运交织在一起。那场灾难里,黎花在洪水中的抉择,成了缠绕她半生的枷锁。而2008年那篇关于“最毒女教师” 的报道,则像一场人造的洪水,将黎敏的人生冲得支离破碎。创作中,他们反复打磨三位女性的“镜像关系”。
“我们想写的不是简单的施暴者与受害者,而是想追问:当一个人的命运被一篇报道、一群网友的愤怒裹挟时,谁该为这场社会性死亡负责?”创作过程中,最让他们纠结的,是如何平衡悬疑与人性的关系。案件是骨,人性是肉,《面纱》里的每一个谜团的背后,都是人性做出的选择,黎花啤酒屋的真实目的、苏眉坠楼的真相、黎敏遗书里的未尽之言,其实都是人性的抉择。他们想借这些人物的命运,画出普通人在时代褶皱里的挣扎与坚守。毕竟,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过“面纱”,有时是为了保护自己,有时是为了原谅过去。
小说的名字“面纱”不可避免地与毛姆的同名经典重名,是因为这个名字精准地击中了他们想要探究的核心——我们用面纱掩饰秘密,用它逃避过去,也用它对抗那些不敢直视的真相。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面纱是透明的,人人似可望见其后的阴影轮廓,却又都心照不宣地维持着那份沉默的模糊。“面纱”之名,也是对这种集体性回避的一个隐喻。
“我们怀着一种希望,希望我们都有勇气揭开面纱,辨认那些我们不敢直视的阴影,也辨认阴影里的自己。”两位作者表示。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陈曦
(主办方供图)
 晋ICP备17002471号-6
晋ICP备17002471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