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独自在夜晚的海边》
是否存在一种至高的力量规定了我们的人生,而我们却一无所知?如果一切都是命中注定,那么生活的意义何在?
这是一个古老而迷人的话题。作为普通人, 我们总是忍住不讨论“命运”,关于自己的,也关于他人的。在西方思想界,这同样是一个历久弥新且十分重要的话题。古往今来,无数的哲人、思想家、神学家、剧作家前赴后继地就“命运是否存在”“自由意志和命运的关系”等话题展开讨论。
在本文中,我们摘录了《存在主义及其他》一书中的《西方大观念之命运》一文,这篇文章系统梳理了西方哲人有关“命运”一题的思辨史,古希腊剧作家探讨人与命运的博弈,基督教神学家激辩上帝与命运的存在,近代哲学家从历史、社会与个人的关系着手,从各种“决定论”来理解人类的生活。
对“命运”的讨论虽出于对未知力量的恐惧以及试图窥探未来的隐秘渴望,但这场前赴后继的讨论本身,既彰显了人在命运面前的能动性和人之为人的高贵与尊严。
陈嘉映先生被称为中国最接近“哲学家”称号的人,同时也是笔耕不辍的译者,他对《存在与时间》的首次译介是文化界的标志性事件。《存在主义及其他》是陈嘉映先生四十年哲学译作精选集,囊括了“语言”“命运”“存在主义”“尼采”“现象学”等经久不衰的哲学话题,每一篇都是极富思想性和思辨性的佳作。
此外,本书还附有几篇陈嘉映先生关于哲学翻译的讨论与心得,哲学爱好者一定不能错过。
人躲不开命运,但也无法强迫运气向他微笑
命运,它有时是个赋有人格的存在,有时是个抽象的概念,无论哪一样,它总是在人生和历史的戏剧中扮演着自由之敌的角色。
至少在古典诗人眼里像是这样。在很多希腊悲剧中,是命运设置好了舞台。一个非要实现的赌咒。一种步步逼近无可转圜的厄运。但舞台上的各个角色却远不是玩偶。在无可逃避的命运笼罩之下,悲剧主人公做出这样那样的选择,他个人的灾难由此而来,而同时他成就了自己命定的生涯。
俄狄浦斯命中注定要杀死自己的父亲迎娶自己的母亲,但并不是命运驱使他去追问自己的过去,去发现自己的罪恶,当他看见了这些罪恶,他决定让自己再也看不见。

《俄狄浦斯王》
降临到阿特柔斯家族的赌咒并没有要求阿伽门农把卡桑德拉从特洛伊带回家去,踏上紫红的地毯。愤怒的复仇女神紧跟着俄瑞斯忒斯不放,但那愤怒是他自己唤醒的,因为他杀害了自己的母亲克吕泰涅斯特拉,而这不是命运让他干的,是他为了替被害的父亲报仇自主而为。
俄狄浦斯离开了自己的出生地,企图借此欺哄命运。按照弗雷泽在《金枝》里的描述,原始部落中实际存在这一类做法。“人们施行拟真的魔法,通过模拟的方式来消除某种邪恶的咒语。这种做法是要用一种伪造的灾难来代替真实的灾难,从而绕过命运的设置。”
古人并不怀疑人们能够选择,靠选择对他们生命的走向施加某种控制。例如,尽管塔西佗承认“大多数人……禁不住相信每个人的未来都在出生的一刻注定了”,但他也说道:“古人中最智慧的人……把选择生活的能力传给了我们。”另一方面,他承认万事自有人力所不能控制的盛衰,尽管说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他发现人们并无一致的看法——不知是系于“漫游的星辰”或“基本元素”,抑或是系于“种种自然原因的结合”。
塔西佗申明,“驾驭人间事务的究竟是命运和不可变更的必然,抑或是偶然机遇”,他本人不加裁决。这等于承认,也许并不是每一件人力不及的事情都是命运使然。有些违乎人愿的事情也许是出于机遇或运道。
“命运”(fate)和“运气”(fortune)有时被当作同义词,只是命运含悲情而运气含喜乐,就仿佛运气总是善意的而命运总是恶意的。然而从人的欲望着眼,命运和运气都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命运和运气远非一事,不过,把两者连在一起也有些道理。它们都为人的自由设了限。人躲不开他的命运,同样,他也无法强迫运气向他微笑。

《奥德赛》
然而,除了在这一点上,命运和运气几乎是相对立的。命运意味着事情一往直前,无可转圜,但唯当有些事情不受必然性的控制才谈得上运气。唯那些可凭机遇发生的事情才会招来运气的青睐。
命运之于运气,看来就像必然之于偶然。倘若万事无不必然,命运就会一统天下。偶然性就会从自然中驱除干净。自然之网中的机会与耦合,连同人生中的自由,就会归化为幻影,人只是由于对无可避免者的无知,对这些幻影情有独钟。
在某种意义上,在对抗命运的搏斗中,运气可说是自由的盟友。好运气似乎能助人成其所愿,还能鼓动人的欲望。即使是坏运气也暗示了机会的存在,既然人很愿相信他能自由地安排自己的生活,那么,坏运气里的机会即使不比命运更友善,至少不那么坚冷。
即使神明也无法逃脱命运的锁链
命运和运气这两个词若替换成必然和偶然,难免会丧失其意味。必然和偶然用在对自然秩序和因果秩序的哲学分析。这组词可以有神学的意味,但不必有。在解说必然和偶然的时候,我们无须涉及超自然的东西。而命运和运气,至少就它们的来源而论,是神学语汇。
在古代诗歌和神话中,命定和机会都赋有人格,要么是神明,要么是超自然力量。有幸运女神,有三位命运女神,她们还有三个恶意的姐妹,或对头,即三位复仇女神。
fate由之而来的那个拉丁词意谓神谕,那是神意认定的东西。命运使然之事是神明所预言的,为奥林匹斯众神会商所决定而不可更改;要么来自宙斯的裁定,而所有其他神明都臣服于他的辖制;要么,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它竟可能是某种超自然的天命,连宙斯也奈何不得。

《众神天堂》
总之,命运观念意味着一种超自然的意志,即使在天命的意义上,仍然意味着那是由一种心智力量所预定的,它不仅能计划未来,而且能实行其计划。因此,命运和天命之所注定,不同于单纯自然的必然性之所注定,在后一种情况中,未来之被决定,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自然而然导致了不可避免的后果。
不过古人看起来并不是极端意义上的宿命论者。在一定程度上,人能取悦神明,诱发神明的妒意和愤怒,就此而言,人的态度和作为看起来也是决定众神如何行事的一个因素。在人间发生冲突的时候,众神有时分头站在冲突的某一方,例如在《伊利亚特》中,或互相敌对,例如在《奥德赛》中,就此而言,我们似乎可以认为世上发生的事情只不过反映了众神之间力量阵营的变化。
神明的意志和计划是在众神之间的争吵中出炉的,但这类意志和计划似乎并非完全无视人的计划和意愿。相反,众神并存似乎使运气本身依赖于奥林匹斯山上的冲突怎样分晓,因而带有相当的偶然性,为人的自我决定多少留下了一些余地。人们能与众神抗争,恰因为众神也许赞同他们,也许反对他们。

《诸神之战》
然而,宙斯裁决万事的终极权能也许更加突出了命运而不是自由。的确如此,而且连宙斯也未见得是他自身命运的主人,更不是众神之中的全能统治者或人类天命的裁判。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合唱队问道:“谁是执掌必然性的舵手?”普罗米修斯答道:“三位一体的命运女神,还有记恨的复仇女神。”
合唱队接着问道:“宙斯不如她们强大吗?”普罗米修斯对此答道:“是的,因为他同样逃不脱命定之事。”合唱队于是追问宙斯命定的灾难是什么,普罗米修斯让他们不要再问了,因为他们已来到奥秘的边缘。后来宙斯自己派遣赫尔墨斯去见普罗米修斯,试图从他口中获取这个秘密,追问“铸成万事的命运”或“不可抗拒的命运铁则”为宙斯注定了何种归宿,普罗米修斯拒绝回答,“他休想这样让我屈服,告诉他命里注定是哪一个将把他赶下暴虐的王座”。
阿喀琉斯留下未答的问题是:如果宙斯能够预见命运为他准备了什么下场,那他是否能够逃脱其厄运。隐含的答案似乎是:没有全知,宙斯尽管全能也无法截断命运的链条。
从“命运”到“决定论”
对命运概念不折不扣地加以接受,就在宇宙之中没给偶然和自由留下任何余地,无论涉及的是上帝的行动,还是自然的秩序,或是历史进程。从而,绝对决定论学说,无论在神学、科学还是历史学中,都是无条件的宿命论。
古代历史学家不是这种意义上的宿命论者。例如希罗多德就见到很多可以用运气的偶然变故或人的选择来加以解释的事情。例如雅典保卫战这一生死决断就被描述为人类选择的行为。雅典人得到的神谕是“难以攻陷的木墙将保卫你们和你们的子孙”,面对这一神谕,他们展现了自己的自由,对这一神谕的意义各抒己见。
希罗多德写道:“有一些年长的人认为,神谕的意思是他们应该把卫城留下,因为卫城在古昔是有一道木栅栏围着的……另一些人则认为神谕里所说的木墙是指雅典的船队,他们认为除了船只,其他什么都不要指望。”地米斯托克利的雄辩使得后一种见解得以实施。为了强调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评论道:“希腊的得救”系于把雅典领向海上强国的这一决定。
直到近代以后,通过黑格尔和马克思,历史哲学才大受必然性的辖制。黑格尔嘲笑一种观点,认为历史是“因果联系的、所谓单纯人类努力和激情的肤浅戏剧”。他同样指责另一些人“空洞地谈论神意和神意的计划”,因为在他们那里,神意的计划是不可测度、不可理解的。
对黑格尔来说,历史是“独独出自精神自由理念的必然发展”。但对于个人和他们的事业来说,这种发展和这种自由完完全全是必然之事。“这些个人始终不过是世界精神的不知情的工具和功能。”

《青年马克思》
对马克思来说,历史似乎同样具有这种必然性。他在《资本论》的序言里写道:他所谈到的个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
他说,他所持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个人不能对他处于其中的社会关系负责,而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
按照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人在历史中的角色已经在历史画卷中写定了。人的自由似乎依赖于人对历史必然发展的了解和听之由之。
历史决定论只是因果必然性统治万物学说的一个部分而已。按照斯宾诺莎、休谟和弗洛伊德等近代思想家的理解,因果性看来是容不得机遇和自由意志的。“上帝并不出自意志自由行事”,斯宾诺莎写道,但“唯上帝是自由因,因为唯上帝存在并出自他自己本性的必然行事”。
说到宇宙中的其他一切,斯宾诺莎认为“没有任何东西是偶然的,万物皆由神圣自然的必然性决定,决定它们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存在并行事”。人也一样,照斯宾诺莎的看法,人无论做什么,“都只由上帝的意志决定”。
休谟由以出发的前提大相径庭,但关于机遇和自由,他所得的结论似乎大致相同。他写道:“我们若对机会加以严格的考察,就会发现它只是个负面的词,它不意谓任何在自然中有点儿踪迹可寻的实际力量。”而说到自由,他认为“若是与必然相对而言,而非与约束相对而言,那么自由就和机遇是同一样东西”。
弗洛伊德与斯宾诺莎和休谟不一样,他不讨论决定论的神学后果或神学预设。在他看来,决定论是科学的基本前提,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可由科学发现的事实。

《弗洛伊德的最后一会》
常被称作“科学决定论”的那种宿命论是盲目必然性的宿命论。它不仅摒绝了自由和机遇,而且也摒绝了最终原因的意图和作用。所有未来事件,无论是自然界的,还是历史的、人类行为的,都完完全全由致动因事先决定;是事先决定,却不是前定,因为并没有什么具有心智的东西在冥冥中引导,没有什么意图有待实现。
康德写道:“宿命体系在斯宾诺莎那里登峰造极,这一体系去除了一切设计的痕迹,自然事物的原始根据不再留存任何智性。”
是否只有这种彻底的宿命论才能和自然科学的原则及成果相谐?威廉·詹姆士曾对此提出质疑。反正这肯定不是唯一能和凡事都有个原因的主张相谐的学说。古代思想家和中世纪思想家肯定自然中存在偶然,肯定人类行为具有自由,而同时并不否认因果的普遍统治。
陈嘉映先生四十年哲学译作精选集
连着原作者的整个思想,通达哲学的另一种路径
发现中介,获得关于自身和世界的理解
原价78元,现仅需54.6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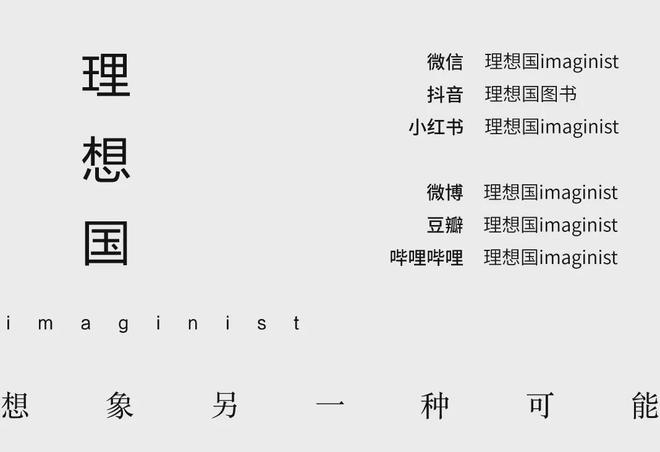
 晋ICP备17002471号-6
晋ICP备17002471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