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我嘛,时间会令人康复,时间会治愈一切。这我知道,这也是最糟糕的事。我不愿意被治愈。”
今天分享的是威廉·特雷弗的短篇小说《我们因蛋糕而醉的日子》。特雷弗是被称为“20世纪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大师,他常写普通人的人生困境,而在这些如梦靥般两难的困境中,我们能窥见人性的幽微之处和人生的真相。
下文节选自《被困住的人》,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我们因蛋糕而醉的日子
文 | 威廉·特雷弗
斯旺·德·莱尔穿着一套皱巴巴的粗花呢西装,手指摆弄着皮带磨损的末端,这条皮带已经在他腰间服务了一年。他在那四百立方英尺的空气中——他们委婉地称之为我的办公室——说了一句调侃的脏话。
我有好几年没见到他了:他是那种经常无缘无故出国的人。顺便说一句,人们可能会认为他的长期缺席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灾难因素,而灾难因素在他性格中起着决定的作用。
看到他站在那里,我就应该知道必须立即提高警惕。在感情脆弱的情况下,我无力招架斯旺打算带给我的任何消遣娱乐。
为了表示对自己的尊重,斯旺从来不会空手而来。斯旺是一个善于发掘生活精华的人;而且他总是把自己精心安排的计划中的一部分慷慨地献给别人。
这一次,他解释说要给我提供一个迷人的下午。对此,我解释说我觉得自己并不想要一个迷人的下午,我太忙了,没办法像他提议的那样消磨时间。但斯旺坐了下来,丝毫不肯动摇;最后,他说服了我。

我写了一张纸条放在我的打字机上:星期二下午。我要做个手术。然后我打了个电话。
“露西?”
“你好,迈克。”
“你怎么样?”
“很好,迈克。你呢?”
“我也很好。我只是想打个电话——”
“谢谢你,迈克。”
“我们必须很快再见一面。”
“是的,必须。”
“我想邀请你共进午餐,但一位重要的老朋友刚才大驾光临。”
“这对你是件好事。”
“嗯,是的。”
“谢谢你打电话来,迈克。”
“再见,露西。”
“再见,迈克。”
斯旺正用一个掰直的回形针在我桌子上画图案。“那不是你妻子。”他说。
“妻子?远非如此。”
“你没结婚什么的?”
“没有。”
“好。我在一家旅馆认识两个姑娘。她们对我说认识你。”我们在九月的阳光下漫步去见她们。
我一直想要一位速记打字员,身材匀称,嘴唇妩媚,头脑很容易被钱币的叮当声打动;在皮特曼公司工作过的快乐女孩,对结婚不抱什么期待。那天下午,我们很可能就是和这样的美女一起消磨时光。后来发现是玛戈和乔,两个给时尚杂志画画的时髦女子。
“我十一岁的时候,”乔告诉我,“写了本儿童读物,还画了所有的插图。有人出版了这本书,当然啦,这让我成了大家都不欢迎的人。”
“你一定非常聪明。”
“不,真的。其实作品非常糟糕,你可以想象。只是碰巧出版了。”
“乔非常看重语言。”玛戈说,“她很有感觉。”
“她有股疯劲儿。”斯旺说。
“看在上帝的分上,斯旺。”玛戈说。
乔和斯旺走在了一起。斯旺觉得无聊,就开始给乔讲一个笑话。
玛戈特意对我说:“乔是我认识的最有才华的人。”我点点头,心里一点也不在意。酒吧里挤满了穿制服的人:深灰色西装,马甲,白衬衫,某个俱乐部或学校的条纹领带。
“喝一杯吗,玛戈?”
玛戈说这是个好主意。我挤到湿漉漉的柜台前,把一张十先令钞票扔在一池啤酒上。我回到玛戈身边时,她说:
“跟我直说吧,你觉得奈杰尔怎么样?”
奈杰尔?为了拖延时间,我抿了口啤酒,却不明白为什么要喝,我实在是很讨厌啤酒。我说:“哦,我喜欢奈杰尔。”
“真的?”
“嗯,他很不错。我的意思是——”
“有的时候,迈克,我觉得奈杰尔是最讨厌的人。”
我想起来了。奈杰尔胖乎乎的,很健谈。不管你想知道什么,奈杰尔都会告诉你。事实上,只要奈杰尔一打开话匣子就没有人能阻止他。奈杰尔是玛戈的丈夫。
我又喝了几口啤酒。凉冰冰的,淡而无味。我什么也没说。
“昨晚我和奈杰尔大吵了一架。”
“哦,上帝!”
玛戈告诉我吵架的事。我垂头丧气地听着。然后我又买了一些酒,这次把啤酒换成了威士忌。有人曾告诉我乔也是有丈夫的。看来这两桩婚姻都要触礁了。
突然,玛戈不再说奈杰尔的事。她斜眼看了看我,说了一句我没听清的话。从接下来的几句话中,我意识到她是在说我会成为一个好丈夫。
“我想是的。”我说。
“我可没有爱上你什么的。”玛戈摇晃着说。
“当然没有。”
离开酒吧后,我们去吃午餐。我在出租车上一直想着露西。

我们去了苏豪区的一家意大利餐馆,太贵了,也不是特别好吃。斯旺跟我们讲他的生活经历,只吃了几个卡萨塔冰激凌。我在楼梯上发现一部电话,就拨通了露西的号码。
“喂,露西。你在干什么?”
“什么意思,我在干什么?我站在这儿跟你通电话呢。”
“我正在苏豪区跟人一起酗酒。”
“嗯,这对你是好事。”
“是吗?真希望你也在。”
露西会觉得无聊的。
“我在读《亚当·比德》。”她说。“是个好故事。”
“是的。”
“你吃午饭了吗?”
“我什么也没找到。吃了几块巧克力。”
“我打电话想问问你怎么样了。”
“我很好,谢谢。”
“我想听听你的声音。”
“哦,别闹了。声音有什么好听的。”
“要我告诉你吗?”
“还是算了吧。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什么时候见个面好吗?”
“我相信会见面的。”
“我酒醒了给你打电话。”
“好的。我得回去看《亚当·比德》了。”
“再见。”
“再见。”
我放下听筒,站在那里看着陡峭的楼梯。然后我走了下去。
“我们现在该做些什么呢?”斯旺说,“四点钟了。”“我想跟迈克说说话。”玛戈宣布,“谁也不许听。”
我在她旁边坐下,她开始磕磕巴巴地小声说话。“关于奈杰尔的事,我想听听你的建议,迈克。”
“说实话,我几乎不认识他。”
“没关系。是这样的,我觉得奈杰尔有点儿不对劲。”
我让她说得具体一点。结果,她把陈述句变成了疑问句。“迈克,你觉得奈杰尔有什么不对劲吗?”
“嗯——”
“有话直说。”
“我告诉你,我不认识他。我只知道他可能装了人造胃。”
“事实上,奈杰尔没有装人造胃。”
“好吧。”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把他想成那样。他的胃一点问题也没有。”
“好吧,那么,这人到底哪儿不对劲呢?”
“我觉得他可能脑子不正常了。”
“那么,看在上帝的分上,带他去看看吧,玛戈。”
“你认为应该?”
“当然。除非你喜欢他脑子有病。”
玛戈咯咯地笑了。她说:“他开始做一些特别古怪的事。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这一切什么时候是个头儿。”
“什么古怪的事?”
“比如把一些老女人带回家。他带着这些女人回家,解释说他和她们一起参加某个会议,把她们带回来喝杯咖啡。真是吓人——奈杰尔后面跟着四五个老太太。她们一待就是很长时间。我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把她们弄来的。他大概以为自己是在做好事。”
“奈杰尔怎么说?”
“他说他们的会议还没有结束。他们只是坐在桌旁写小纸条。谁都不说话。”
“我觉得这一切很有意思。我相信肯定有个非常简单的解释。我认为你没有好好调查此事,玛戈。”
“我们离开这地方吧。”斯旺说。
我们去了另一个地方,叫蓝山羊。这是一个可以下午喝酒而不用看脱衣舞的俱乐部。玛戈还想继续谈奈杰尔的事,但我坚决地说不想再听奈杰尔的事了。我和乔聊了起来。
“乔,”我说,“你认识一个叫露西·安斯特拉斯的姑娘吗?”
“矮矮胖胖,有点秃顶?”
“不。露西是个非常漂亮的人。”
“不是同一个姑娘。”
“高个子,皮肤白皙,眼睛非常蓝。动作像猫一样。”
“不认识。”
“她总说一些出人意料的话。她好像是半个瑞典人。”
“迈克,你能猜到我是半个威尔士人吗?”
“猜不到。我想问问你露西的事——”
“但我不认识她。”
“我不知道该拿露西怎么办。”
“你说话的口气像玛戈。玛戈不知道该拿奈杰尔怎么办。没人知道该拿别人怎么办。上帝!我可以再来点伏特加吗?”
“是的。就像我说的——”
“我要三份伏特加。”
我点了伏特加。斯旺和玛戈心事重重地坐在我们旁边,一声不吭;他们甚至没有听我们在说什么。玛戈注意到我的目光,张开嘴想说话。我转过身,把酒水递给乔。
“玛戈的丈夫有点不对劲。”乔说,“可怜的玛戈担心极了。”
“是的,我都知道。玛戈告诉我了。”
“我喜欢奈杰尔,你知道。”
“也许你能帮他改过自新。我们刚才在谈别的事。我告诉你——”
“似乎奈杰尔带女人回家。”
“是的,我知道,乔。”
“对玛戈有点过分。”
玛戈听到了这话。她喊道:“什么对玛戈过分?”然后,谈话就变得有一搭没一搭。
我去给露西打电话。“露西?”
“喂。是迈克吗?”
“是的。”
“你好,迈克。”
“你好,露西。”
“你怎么样?”
“我感觉有点不舒服。可是,露西?”
“怎么了?”
“我不是想要逗乐子。我不是在开玩笑。”
“你在哪儿?”
“在蓝山羊。”
“哪儿?”
“用豹子皮做装饰的那家。乔、玛戈和斯旺也在。”
“他们是谁?”
“另外几个人。”
“我很高兴你打电话来,迈克。”
“玛戈的丈夫奈杰尔带女人回家。我想知道你是不是有什么建议,我可以告诉她。她很担心那些女人。她们成群结队地来。”
“哦,迈克,我不太清楚这种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说实在的。”
“对不起,露西。我以为你可能知道。”
“门铃响了。再见,迈克。如果我是你,我就回家去。”

斯旺说他想喝茶。我们离开蓝山羊,顶着明晃晃的阳光向弗洛丽丝走去。
玛戈又说起了奈杰尔。
斯旺说他认识一个人,能给奈杰尔带来很大帮助。他不记得那人提供了什么治疗,只说人们对他评价很高。
我去给露西打电话。“露西?”
接电话的是一个男人的声音。我说:“我可以跟露西说话吗?这个号码没错吧?”
男人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露西拿起了话筒。“迈克,又是你?”
“喂,露西。你好吗?”
“我很好,迈克。”“好的。”
“迈克,你四点一刻给我打过电话。你知道现在几点吗?”
“现在几点?”
“四点三十五分。”
“我惹你厌烦了,是吗?”
“没有,没有。只是,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吗?我的意思是,你是不是想要什么又觉得难以启齿?”
“我感到无聊,和这些人在一起,露西。”
“是吗?”
“在你公寓里的那个人是谁?”
“一个叫弗兰克的朋友。你不认识。”
“他在那儿做什么?”
“你什么意思,他在做什么?”
“嗯——”
“你听着,我问问他。弗兰克,你在做什么?”
“他怎么说?”
“他说他在泡杯茶。”
“我也在喝茶。在弗洛丽丝。真希望你也在。”
“再见,迈克。”
“别走,露西。”
“再见,迈克。”
“再见,露西。”
回到其他人身边时,我发现他们在哈哈大笑。斯旺说他们吃的蛋糕把他们弄醉了。“你闻闻。”他说。蛋糕有一股朗姆酒的气味。我尝了一些:味道也像朗姆酒。我们都吃了很多蛋糕,一想到吃蛋糕会醉就忍不住大笑。我们又点了几份,对侍者说很好吃。
等热情稍稍减退一些后,斯旺说:“迈克,关于玛戈丈夫的事,我们需要你的建议。”
“我已经告诉玛戈——”
“不,迈克——说正经的。你了解这些事情。”
“你凭什么认为我了解这些事情?我不了解这些事情。”
“好吧,迈克,我来告诉你。玛戈的丈夫奈杰尔总是带一群老女人回家。玛戈担心事态会进一步发展——比如,流浪汉、杂货商、断腿的士兵什么的。你觉得她应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玛戈应该怎么办。玛戈,我不知道你应该怎么办。要么干脆去问问奈杰尔他想干什么。现在,再吃点蛋糕吧。”

“这下有主意了。”斯旺兴奋地喊道,“亲爱的玛戈,你为什么不问问老奈杰尔他想干什么呢?”
乔用又大又尖的手指在我脸上亲热地砍了一下。我猜是为了表示赞赏而不是攻击,因为她是带着微笑这么做的。
“但奈杰尔只是说,”玛戈说,“他们的会议还没结束。”
“啊,是的,”斯旺说,“但你没有逼问他。你没有说:‘什么会议?’你没有表现出对他们的关键业务一无所知。奈杰尔很可能以为你毫无疑问地接受了整件事,对婚姻生活没有什么其他期望。你刚才上厕所的时候,”斯旺对我说,“玛戈承认她很担心。”
“她之前也向我坦白过。我没有上厕所。我去打电话了。”
“我可以这么做吗?”玛戈说,“我可以给奈杰尔打电话,让他解释这一切吗?”
我们都点点头。玛戈站起身,犹豫了片刻,又坐下了。她说她办不到。她解释说她太害羞了,没法用这种方式给丈夫打电话。她转向我。
“迈克,你来好吗?”
“我?”
“迈克,你能打电话吗?”
“你是想让我给你丈夫打电话,询问他跟那些我完全不认识的老女人的关系?”
“迈克,拜托你了。”
“想想那我要做多少解释吧。想想这团乱麻。奈杰尔会以为我是其中一个女人的丈夫。奈杰尔会以为我是警察。奈杰尔会问我一个又一个问题。看在上帝的分上,你凭什么认为我能从他嘴里问出什么答案呢?”
斯旺说:“你只需说:‘是奈杰尔吗?听着,奈杰尔,我听说那些女人不分昼夜地去你家,这是怎么回事?’就说你代表养老金部。”
“我不可能称呼那男人奈杰尔,然后说我是养老金部的人。”
“迈克,玛戈的丈夫就叫奈杰尔。你叫他奈杰尔完全没问题。如果你不称呼他奈杰尔,他会对你说去你妈的。他会说你打错电话了。”
“所以我就说:‘你好,奈杰尔,我是养老金部。’那人准会以为我疯了。”
玛戈说:“迈克,就按你自己的意思去做吧。不要理会斯旺。斯旺蛋糕吃多了。去吧,你知道电话在哪儿。”她给了我一张写着号码的纸。
“哦,上帝。”我说。我再也无法忍受,就借了四便士,大步朝电话机走去。
“喂?”电话那头的声音说。
“喂。我能和露西说话吗?谢谢。”
“喂。”露西说。
“喂,露西。”
“有事吗?”露西说。
“我是迈克。”
“我知道你是迈克。”
“他们要我给刚才跟你说的那个男人打电话,但我不能这样随随便便给人打电话——”
“你为什么不回家睡觉?”
“因为我睡不着。还记得那个跟老女人在一起的男人吗?唉,他们让我给他打个电话,问他想干什么。露西,我做不到,对吧?”
“是的,说实在的,我不相信你能做到。”
“他们叫我冒充养老金部。”
“再见,迈克。”
“等等——露西?”
“怎么了?”
“那个男人还在吗?”
“哪个男人?”
“你公寓里的那个男人。”
“弗兰克。他还在。”
“他是谁,露西?”
“他叫弗兰克。”
“对,但他是做什么的?”
“我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弗兰克,你是做什么的?靠什么谋生?他说他是——什么,弗兰克?货运代理,迈克。”
“货运代理。”
“再见。”
“再见,露西。”
我回到茶桌旁时,每个人都很高兴。没有人问我奈杰尔说了什么。斯旺付了账单,说特别想带我们去尤斯顿的什么地方看一场东方恐怖展,然后带我们去一个派对玩玩。
在出租车里,玛戈说:“奈杰尔说了什么?”
“他不在家。”
“没人接电话吗?”
“一个女人接了电话。她说我打扰她们开会了。我说,开什么会?但她想先弄清我是谁再回答。我说我是养老金部的,她说声‘哦,上帝’就把电话挂了。”
我们去参加派对早到了几个小时,但似乎谁都不介意。我帮一个穿休闲裤的女人把一瓶瓶的葡萄酒倒进一个坛子。斯旺、玛戈和乔在玩一台录音机,过了片刻,那女人的丈夫来了,我们便出去吃饭。
大约八点钟的时候,人们开始陆续到来。空气里弥漫着烟味、音乐声和汽车的尾气;然后,派对开始以一种足够欢快的节奏向前推进。一个头发打着卷儿的女孩满腔热忱地跟我谈论爱情。我想她一定有着跟我同样的感觉,但我没有把她想象成一个灵魂伴侣,哪怕暂时的也不行。
她说:“在我看来,每个人都有一种品质可以让爱情变得更美好,变得更强大。比如自尊。或诚实。或道德上——甚至智慧上,甚至情感上——的正直。让两个人相爱。唯一能把事情搞砸的是其中一个人的品质。其他人根本不参与其中。除非以一种迂回的方式——比如,被嫉妒所控制。你同意吗?”
我完全不能确定,但我说同意。
“爱情还有一点,”头发打着卷儿的女孩说,“就是独特的感染力。你有没有想过,当你爱上某人的时候,其实内心希望自己也被爱?不用说,这就是自然规律。我的意思是,如果每次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却都得不到爱的回报,就会很反常。这种可能性只占很小一部分。”
一个咄咄逼人的年轻人听到这话,放声大笑起来。他继续笑着,看看那个头发打着卷儿的女孩,又看看我。
我离开了,用坛子里的酒把我的杯子倒满,然后问一个漂亮的中年妇女是做什么的。她的回答忸怩作态;我笑了笑,走开了。
玛戈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拖到一个角落里。“迈克,你再给奈杰尔打个电话吧?”
“我一直在考虑这事。”我说,“说实话,我觉得我不能插手。”
“哦,可是,亲爱的,你答应过的。”
“答应?我什么也没有答应。”“哦,迈克。”
“说真的,整个这件事——哦,好吧。”“现在,迈克?”
“好吧。现在。”
“露西?”
“是迈克吗?”
“还会有谁?”
“到底是谁?你现在在哪儿?”
“我在一个派对上。”
“是一个正经派对吗?”
“是的,我想是的。你干吗不一起来呢?”
“我来不了,迈克。我手头有事情。”
“我想,是陪那个该死的货运代理吧。”
“什么代理?”
“货运。你那个货运代理朋友。弗兰克。”
“他不是货运代理。他是做出版的。”
“那他为什么说自己是货运代理?”
接着是一番长篇大论的解释。自称货运代理只是弗兰克的一种幽默自嘲。我琢磨着这件事,返回去找玛戈。
“他怎么说,迈克?”
“一个女人说奈杰尔不在家。”“就这些?”
“我说目前房屋正受到监视。我说地方当局非常不满意。”
“她怎么说?”
“她开始抱怨,我说了句‘我是认真的’,就把电话挂断了。”
“谢谢你,迈克。”
“没关系。有事随时吩咐。”
斯旺来到我们身边,玛戈说:“迈克又给奈杰尔打了电话。迈克太棒了。”
斯旺拍了拍我的后背,说:“有什么乐子吗?”
玛戈开始告诉他。我走开了。
乔假装在听两个男人讲一个复杂的故事。她压低声音对我说:“别担心玛戈。我会让她摆脱出来的。”
我盯着她,不明白她凭什么认为我在担心玛戈。“我相信你会的,乔。”我说。
“相信乔吧。”她小声说。
我说我认为她是个值得信赖的人。我开始详细阐述这个想法。其中一个男人说:“不介意吧,老伙计?”
我耸了耸肩,挤过人群,走回电话机旁。为了确保无误,我拨了三次号码,但每次都无人接听。
此刻,人们开始三三两两地跳舞。我在坛子旁停住脚步,发现身边又是那个头发打着卷儿的女孩。她对我笑了笑,我用一种很无趣的口吻说:“你认识一个叫露西·安斯特拉斯的女孩吗?”
头发打着卷儿的女孩摇了摇头。“我应该认识吗?”
“我想也不认识。”我说。女孩仔细打量了我一番,走开了。
我上了楼,找到一个安静的房间,里面有一张床。梳妆台上的一盏灯发出微弱的光。床看起来很舒服,几乎笼罩在黑暗中。我在床上摊开四肢,享受着这黑暗。片刻后,我睡着了。
醒来时,我手上的夜光表显示我睡了两个小时。两个女孩在梳妆台前洗脸。她们从手提包里掏出印着马的头巾,戴在头上。她们悄声耳语,然后离开了房间。我躺在那里,思考这一天发生的事情,想知道吃早餐时我对它们有什么感觉。我总觉得吃早餐时对前一天的感受至关重要。
一个端着酒杯的男人走进房间,站在梳妆台的镜子前。他梳理了一下头发,紧了紧领带。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缠在右手食指上。他把食指塞进每个耳朵来回转动。他一边查看手帕,一边兀自评论这番操作的结果。我闭上眼;待我睁开眼睛时,他已经不见了。我点燃一支烟,又去打电话。
“谁呀?”一个声音说。是那个做出版的男人。我要求和露西说话。
“喂,露西。”
“哦,迈克,说真的——”“露西,那男人又来了。”“我知道,迈克。”
“现在是凌晨两点。”
“凌晨两点。对不起,迈克。”她的声音那么温柔,于是我说:
“别再假装不伤害我了。”“我想我还是挂电话吧。”“要挂我挂,妈的。”

我站在电话机旁,思考着,心头一阵难受。我感觉到手指间有什么东西,低头看到了那张写着奈杰尔号码的纸。我拿起听筒,拨了电话。
我等了差不多一分钟,然后一个女人的声音说:“喂?请问是哪位?”
我似乎说了句:“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女人立刻说道:“你是谁?你打错电话了。”
“没有打错。”我毫不客气地回答,“请叫奈杰尔来接电话。”
“奈杰尔在主持会议。你这个要求会打断我们的会议。议程上的内容很多。我没法满足你,先生。”
“这里是养老金部。”我说,我听到女人吃力地喘气。然后她挂断了电话。
我挤过派对的人群往回走,寻找大门。我心想,所有的事情都或多或少地解决了。玛戈的怨气已发泄出来;她感觉好多了,现在大家要做的只是询问奈杰尔想干什么,并一直追问下去,最终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至于我嘛,时间会令人康复,时间会治愈一切。这我知道,这也是最糟糕的事。我不愿意被治愈。
我希望我对露西疯狂的爱能继续从梦中突然向我袭来;从喝了一半的酒杯里嘲笑我;猝不及防地扑向我。随着时间的推移,露西的脸会模糊成一个小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在街上遇见她时,会漫不经心地跟她打招呼,和她一起喝咖啡,静静地谈论我们上次见面后桥下的流水。
今天——甚至不是今天,因为已经是明天了——会像其他日子一样悄悄溜走。它不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不是我孤注一掷的日子。不是我一生的挚爱被夺走的日子。
我打开大门,望着外面的夜色。天气很冷,令人不适。我喜欢这感觉。我讨厌那一刻,同时也爱着它,因为那一刻我仍然爱着露西。
我小心翼翼地推上门,把黑暗和细雨关在门外。我回到派对上时,所有遗忘带来的忧伤刺痛了我。我想,时间已经在起作用了;时间正在嘀嗒嘀嗒把她带走;时间正在销毁她,正在扼杀我们之间的一切。
随着时间对我的作用,我会没有痛苦、不带感情地回顾这一天。我只会记得它是虚无易碎的表面上的一道闪光,是一个蛮有趣的日子,是我们因蛋糕而醉的日子。
本文摘选自
《被困住的人》
副标题: 威廉·特雷弗短篇集1967—1992
作者: [爱尔兰]威廉·特雷弗
译者: 马爱农
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品方: 浦睿文化
出版年: 202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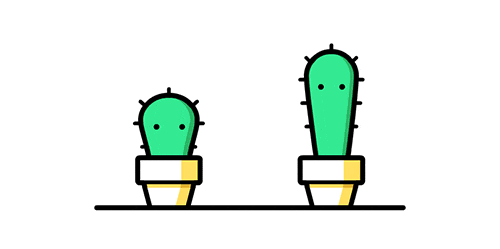
编辑 | 串串
主编 | 魏冰心
配图 | 《双重赔偿》《了不起的盖茨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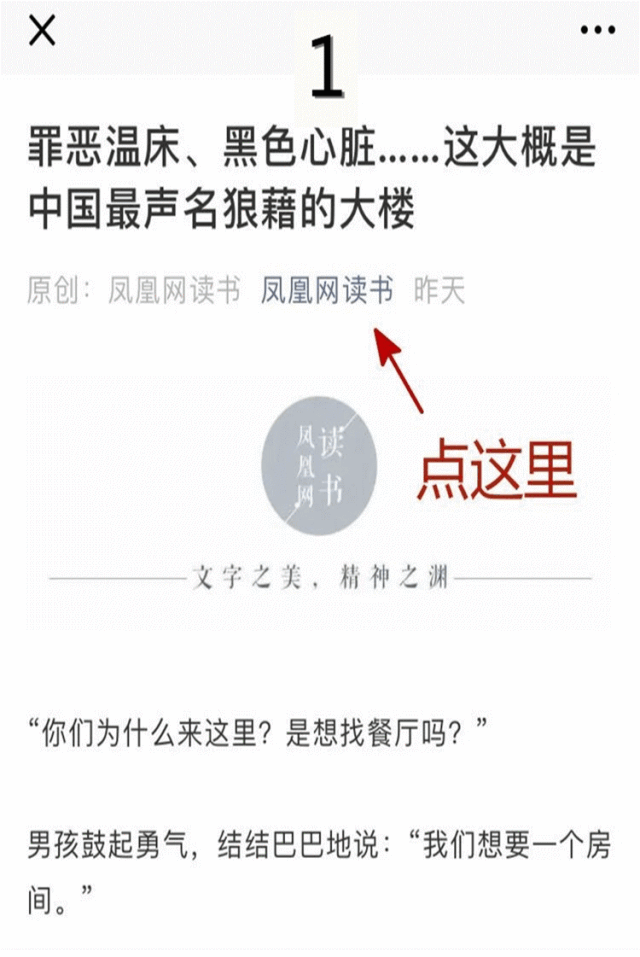
知识 | 思想 凤 凰 读 书 文学 | 趣味
 晋ICP备17002471号-6
晋ICP备17002471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