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作家吴君的小说集《阿姐还在真理街》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作家吴君近五年来发表在期刊上的中篇小说,包括《小户人家》《你好大圣》《结婚记》《万事如意》《好百年》《阿姐还在真理街》,以六个从嘈杂市井中、从平凡家庭里生长出来的故事,记录深圳这座城市的世相百态、时风嬗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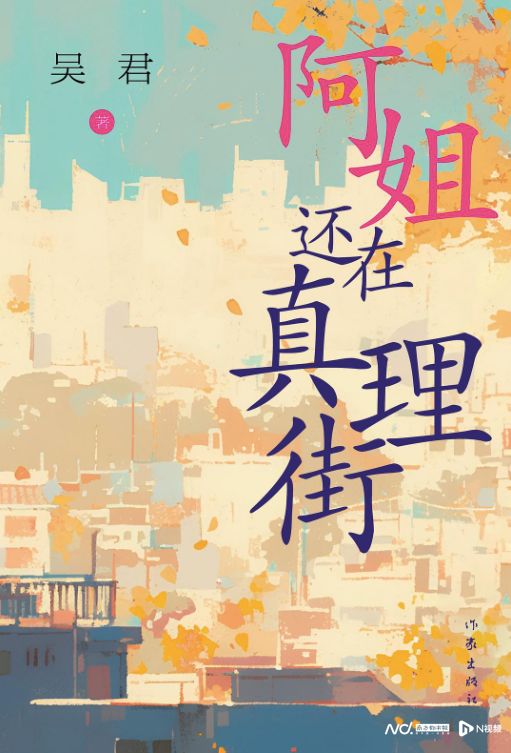
其中,首发于《人民文学》2023年第3期的《万事如意》获得2023年度人民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授奖辞称:“父与子、夫与妻的矛盾,揭开了家庭原有的温情面纱,也使每个人自现原形,而这又让他们逐渐意识到自身的问题,转而切实面对时世流变,以求万事如意。争执激化了潜在的冲突,也提供了和解的契机。由此,一桩看似嘈嘈切切的家常故事,又有平地一声雷的震撼,凸显出作者别致的叙事能力与强劲的艺术腕力。”
吴君原是河北泊头人,大学毕业后南下深圳工作定居。她做过记者,当过公务员,现为深圳市作家协会主席,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以《亲爱的深圳》为代表,吴君早年的写作聚焦于在深圳打拼的小人物,着力于探索在光怪陆离的大都市现代化语境中人们面临的身心异化和精神困顿,文笔泼辣粗粝,被评论界认为是“一份来自生活前沿的报告”。2000年以后,吴君的目光转向深圳的移民群体,“一次移民,终身移民,后代也多是移民的命运”,作家敏锐地觉察到在深圳的外省人内心的不安与躁动,以及外来移民和原住民之间在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冲突矛盾,《二区到六区》《复方穿心莲》等一系列作品,集中为在深圳的移民群体画像立传,力透纸背的现实主义笔调引起文坛的广泛重视。近年来,吴君的深圳叙事有了更加复杂曲折的面相,写的依然是底层小人物,新移民与老深圳的对峙依然若隐若现,但作家讨论的却是更广泛的人生命题:如何不被庸常琐碎的生活磨平棱角?如何在快速迭代的时代里保持个体的尊严?如何面对中年危机、青年危机,甚至童年的原生家庭危机?如何在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一腔赤诚地活着?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她还常常写到一些过时的人、被抛弃的人、无所事事的人、随波逐流的人……这些人的失意失落,闲散无助,和深圳高歌猛进的城市形象形成强烈的对照。然而所有的人物又不是单薄的,框架式的,哪怕疲沓惫赖,也有着一种来自街头巷弄、血气充沛的鲜活感。《阿姐还在真理街》收录的几个中篇小说,正是这一时期写作的代表。
“写作是一个作家暴露短板的过程,也是一个作家认识自我的过程,是梳理和反思的过程,也是不断成长的历程。”吴君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谈道,“作家的成长过程是漫长的,需要长期的积累和实践。”如果说二十多年前,她已野心勃勃想要“绘一个文学的深圳版图”,如今,这个版图已渐次肌理清晰、立体丰满。她打量深圳的眼光并非是一味熟稔和亲密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她的小说里呈现的人与时代、人与城市的关系更加幽微透彻,启人深思。
南都专访深圳作协主席、作家吴君

深圳作家协会主席、作家吴君
南都:《阿姐还在真理街》里收录的几个中篇小说写于什么时间段?
吴君:近五年来发表在期刊上的中篇小说。
南都:《阿姐还在真理街》里收录的小说,主角大部分是深圳的新移民(也包括来深圳的底层打工人),您为什么持续关注深圳的这个群体?您通过什么途径观察和了解他们?
吴君:创作上我确实做过一些规划。如同一个司机,必须知道自己途经哪里和目的地。“三来一补”时期,我写过流水线工人的精神出路和他们的内心世界,如《亲爱的深圳》《陈俊生大道》《小桃》《扑热息痛》等。千禧年我写过移民和本地人的冲突与和解,多数都是用中篇来完成的。比如《红尘流动》《有为年代》《不要在太阳下面哭泣》《不要爱我》《樟木头》《复方穿心莲》《蔡屋围》等等。再后面就是城市化进程中的系列小说《当我转身时》《阿姐还在真理街》《莲塘饭店》《生于东门》等。然后一路写下来,写到今天。
南都:在您对深圳故事的书写中,矛盾冲突总是发生在外来移民和原住民之间,例如《小户人家》里的黄培业瞧不上关外的原住民曾海东,《阿姐还在真理街》里的姜兰惠最初也是以教育者、拯救者的身份出现,让陈家兄弟“走上正途”。我们都知道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为什么外来者和原住民之间的矛盾如此不可调和?经历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这些矛盾是否有所缓解?
吴君:我认为矛盾并不会因为社会进步而消失。
南都:这部小说集里还涉及深圳的一个社会现象,即女多男少的问题,所谓“总有几个女的在抢一个渣男”。这个现象是怎么引起您的注意的?您怎么看待。当代深圳的婚恋市场和青年人的婚恋观?
吴君:可能是我所处的环境中一个特殊的状态吧,我认为这是一个历史阶段,没办法用是非好坏来评判。
南都:您认为《阿姐还在真理街》这部中篇小说集和此前的《从二区到六区》《我们不是一个人类》《亲爱的深圳》等作品相比,从题材到风格有哪些不同之处?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您对文学,对人性和对世界的看法发生了哪些改变?
吴君:写作是一个作家暴露短板的过程,也是一个作家认识自我的过程,是梳理和反思的过程,也是不断成长的历程。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储备不足,都将影响作家的心态和作品的深度、广度。作家的成长过程是漫长的,需要长期的积累和实践,这就需要作家们在生活中扎下根来,在一次次磨练中掌握创作要领,并贯穿到一个作家的整个创作生涯中。到现在为止,我出版过14部小说集,也发表了300多万字小说。写作这件事令人愉悦,因为获得了某种神秘的体验和成长。所谓的改变应该体现在每个时期不同的小说里。
南都:其实我在这部小说里,还看到另一个重要的主题——中年危机。无论是职场不得意的黄培业、魏东海,还是面临家庭困境,觉得自己的一生十分失败的姜兰惠,他们的困顿痛苦,读来都让人感同身受。深圳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城市,甚至职场也有35岁“预警线”,在这样一个高歌猛进的环境里,中年人应该如何自处?
吴君:黄培业在事业受挫中,又被魏东海釜底抽薪,领导的红人魏东海被迫改行,江兰惠以为遇见了爱情却遭遇家暴,中年危机,青年们在卷,童年也会有阴影。令人感到狼狈的现实谁也逃不掉。创作中,我在意的是有没有违背生活逻辑。
南都:这部小说集中有一些生动的粤语方言,例如“蹿”“心情不靓”“大晒”等等。对于方言在小说中的使用,您有什么考量?期待达到怎样的艺术效果?
吴君:电视剧《繁花》大火之后,我在反思普通话的单调和方言的魅力。我在两部长篇中大量使用了方言,这让我感到与人物非常贴合。我小说中的人物在他所处的环境里不可能字正腔圆谈论时政,看《红楼梦》,谈论具体生活之外的话题。家常话合我的心,用粤语表达纯属文体的需要。
南都:作为一个来自北方的新移民,您是否认为自己已经真正融入了深圳这座城市?在您的生活和文字里,是否还有北方家乡的痕迹?
吴君:我现在到了怀旧的年龄,只是怀的不是故乡,而是深圳的当年。移民话题如果放在20年前的深圳,会非常切合。现在的我不认为移民这个标签还在我们这些中年人身上贴着。被排斥和身处异乡的感受,应该不是我们当下的境遇,它只是一种宝贵的人生体验,发生在当年。
南都:作为广东省作协副主席,深圳作协主席,请谈谈深圳当代文学创作生态和面临的挑战。
吴君:文学深圳是溢出文学史框架之外的状态,是难以归类的写作,因为杂糅,难以归类,所以也就比较吃亏,可是他结结实实地长在了这里,新鲜、蓬勃、是最具活力和生长性的写作。在我看来,深圳文学是大湾区文学的新样态,新表达上最充分的城市。需要进入主流评论的视野,还有很多年轻、才华和实力相当的作家,需要文学期刊和评论家们的支持和帮助。
南都:你并不是一名职业作家,创作量却非常大,除了克服时间上的问题,如何处理质和量的关系,未来有什么写作计划。
吴君:201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了我一本小说集,需要附个创作年表。我第一次去整理自己这些年的小说,虽然也还是漏掉了一些。当我发现自己有一百多篇小说的时候,还是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有些人认为写得多就会写得烂。可是很快我就想明白了。我认为写是最重要的,因为很多问题都是在写的过程中解决的,而不是想就可以了。就像你学了很多游泳的理论,可是没有下过水,喝过水,怎么能学会呢,这是量变和质变的关系。尽管我会认真对待每一篇,但同时我也不纠结在具体的某一篇,因为我是宏观地写作,完成我一个整体写作计划,具体的每一篇只是我写作版图上的一篇,它代表的只是我的一个时期。写作不是短跑,而是马拉松。前提是认准了这条路,然后坚定不移。
吴君简介:代表作《亲爱的深圳》《万福》;出版专著14部,其中2部小说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公映。曾获人民文学奖、中国小说双年奖、百花文学奖、北京文学奖、小说选刊奖、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广东省“五个一工程”奖等。
采写:南都记者 黄茜
 晋ICP备17002471号-6
晋ICP备17002471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