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学本是入世的,但后世所称的“汉学”“宋学”却以“终日不出于轩序”(欧阳修《答吴充秀才书》)也即“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近人韩儒林)的“出世”为特色,今天则称为“纯学术”或“为学术而学术”。西哲康德的先验美学中有超功利的“纯粹美”与功利的“依存美”之分,这“依存美”,我认为正可对应入世的儒学。
出世的儒学和超功利的艺术当然是高端的社会需要,但入世的儒学和功利的艺术更是大众的社会所需。
从孔子、孟子到韩愈、欧阳修至清代的浙东学派,经世致用始终是儒学的根本目标。儒学经典的学习、传播,是为了实现“天下归仁”的理想,其具体的学习方法便是《论语》所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然后“知之则习之”“不知则不作”——意为看懂了便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工作实践中去,看不懂的地方便暂时让它去,不要钻牛角尖。其具体的运用方法是《中庸》的“道不远人”,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孟子》则说“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意为从身边容易的事做起,积累起来,远大而艰难的事业也就可以实现了。孟子又说:“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像孔子这样伟大的人物,当他做仓库保管员时,便努力做好出入的账目。当他做畜牧饲养员时,便努力把牛羊养得茁壮——无论地位卑微还是显赫,每一个人都做好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便都是对实现“天下归仁”理想的贡献。

正是因为基于这样的学习方法和运用方法,所以,对每一个人都是“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从而,也就是“人皆可以为尧舜”了。
所谓“六经皆史”,所谓“士,事也”,“史”即“事”。所以儒家的经典文献也好,儒家的各色人等也好,都在于社会建设的具体工作。离开了为社会做事,儒学便失去了入世的意义,迄至宋代,经世致用的儒士主要的精力在于为社会做事,“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对“纯学术”的儒生虽有所反驳,但用力不大。而清代的浙东学派包括颜李学派、常州学派,他们的经世致用,主要的精力却不再是为社会做事,而是在倡导经世致用,反驳“为学术而学术”的“汉学”和“宋学”——兹不赘,容后述。
“汉学”和“宋学”的名词都是清人所起的。
“汉学”指始于汉代的儒家学派,主要指“经古文学派”,以郑玄、马融、刘歆、贾逵等为代表,其特点是埋首于书斋之中,扎扎实实地训诂、考据、整理、辑佚儒家的经典。原来,经过秦火的焚劫,进入汉代,儒家的典籍所剩无几,虽陆续有所发现,但亟须加以梳理传疏,否则便难以使人明白其义。但由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家的解释颇有曲解其义的,愈加令人“不明觉厉”。
历魏晋、隋唐而宋元明,至乾嘉学派,这一学派达于集大成的登峰造极,体系的庞大,实开今天的学术研究之先声。相比于经世致用的儒学“知之则习之,不知则不作”的学习方法和做事原则,一是“知之则疑之,不知求知之”,二是儒学的“道”在经典的文字之中,不在为社会做事的实践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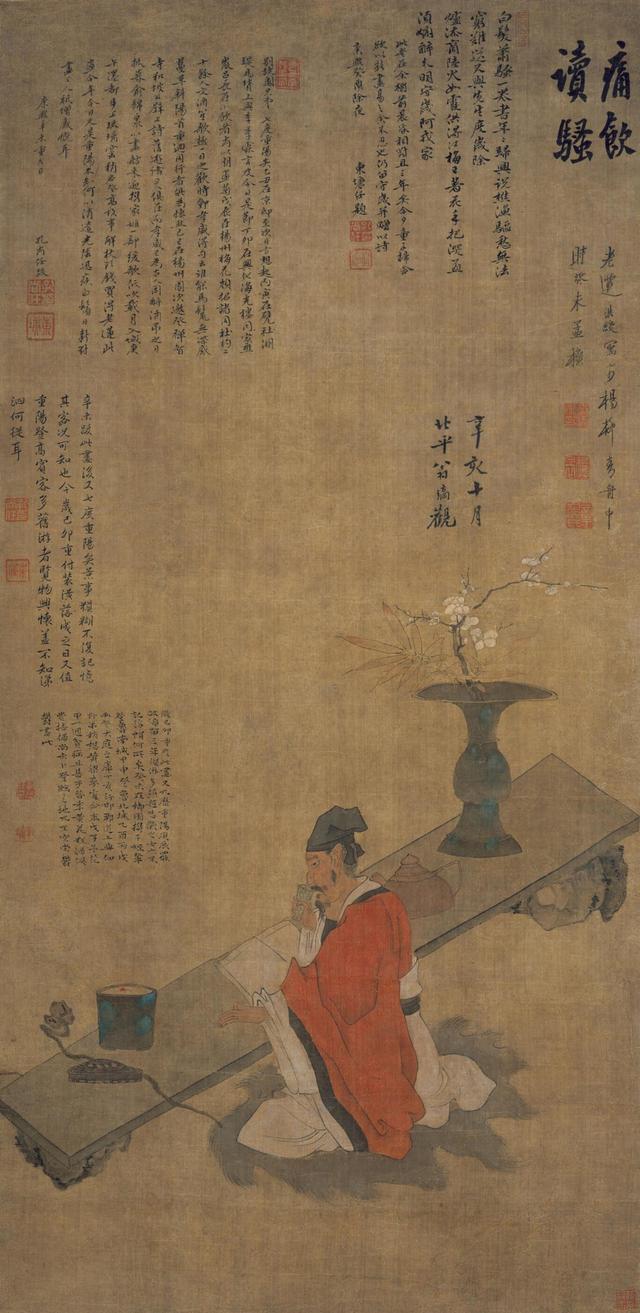
什么叫“知之则疑之,不知求知之”?儒学经典中的某一句话,大家都这么认为的——应该不会这么简单吧,一定另有高深含义吧?于是穷尽精力去怀疑它、推翻它,提出自己独到的理解;大家都不明其义的,我更要钻牛角尖,努力地去诠释它,把它玄奥的精义研究出来——最终所形成的“研究成果”,他们自以为是得“道”了。当时后世的“学术界”也公认为是得“道”的典范,自然也就不必、事实上也没有时间精力再去为社会做事了。不仅如此,更以这样的“纯学术”比之经世致用的“功利学术”足以代表儒学之“道”。
然而,欧阳修却认为经世致用的儒学之于道,可以“何其用功少而至于至”;“汉学”之于道,用功于经典的言语文字,“愈勤愈力而愈不至”“余尝哀夫学者,知守《经》以笃信,而不知伪说(诸儒措其异说于其间)之伪《经》也”。苏洵则表示:“(圣人之说)汩而不明者,诸儒以附会之说乱之也,去之,则圣人之旨见矣。”苏轼更认为不过是“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
其实,宋人对“汉学”的批评,早在南北朝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中便有反复提醒,如“空守章句,但诵师言,施之世务,殆无一可”,又“圣人之书,所以设教。但明练经文,粗通注义,常使言行有得,亦足为人。何必仲尼居即须两纸疏义?燕寝、讲堂,亦复何在?以此得胜,宁有益乎?光阴可惜,譬诸逝水,当博览机要,以济功业。必能兼美,吾无间焉”。同样是主张“学而时习”而质疑过度研究的意思。
至清代的乾嘉学派,“汉学”成为“儒学第一流的学问”,尤以开山阎百诗为典型,其子阎咏记其治学的方法说:“府君读书,每于无字句处精思独得,而辩才锋颖,证据出入无方,当之者辄失据。常曰:‘读书不寻源头,虽得之,殊可危!’手一书至检数十书相证,侍侧者头目为眩,而府君精神涌溢,眼烂如电,一义未析,反复穷思,饥不食,渴不饮,寒不衣,热不扇,必得其解而后止。”他自己则说:“古人之事,应无不可考者,纵无正文,亦隐在书缝中,要须细心人一搜出耳。”穷四十年精力专注于治学研经,成《古文尚书疏证》考定古文为伪,被公认为经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此后如戴震、惠栋、章太炎等,无不以板凳十年的不涉世事、穷研极讨为儒学的正宗大道。如焦循治《周易》,闭关四十年,连亲友间的庆贺、哀悼也一概视作“俗事”而摒绝,其专心致志于治学的精神可见一斑!
至于他们所取得的学术成果,第一个特点是庞大、高端、精深,第二个特点则是艰涩、难懂、无用。这里举一个例子。章太炎早年宗浙东学派,投身革命,后来钻进象牙塔,致力于经学和小学,世人所推崇的是他后期的学术,鲁迅先生则极推其前半生的革命生涯,对他的“纯学术”则表示“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其实何止“那时的青年”,就是今天专门研究章太炎学术的专家们恐怕大多也是如此。而令人震撼于章太炎学问之高大精深的,甚至不在于他皇皇的著述,而在于他分别以四个“乂”、四个“又”、四个“工”、四个“口”为四个女儿取名,差一点使她们嫁不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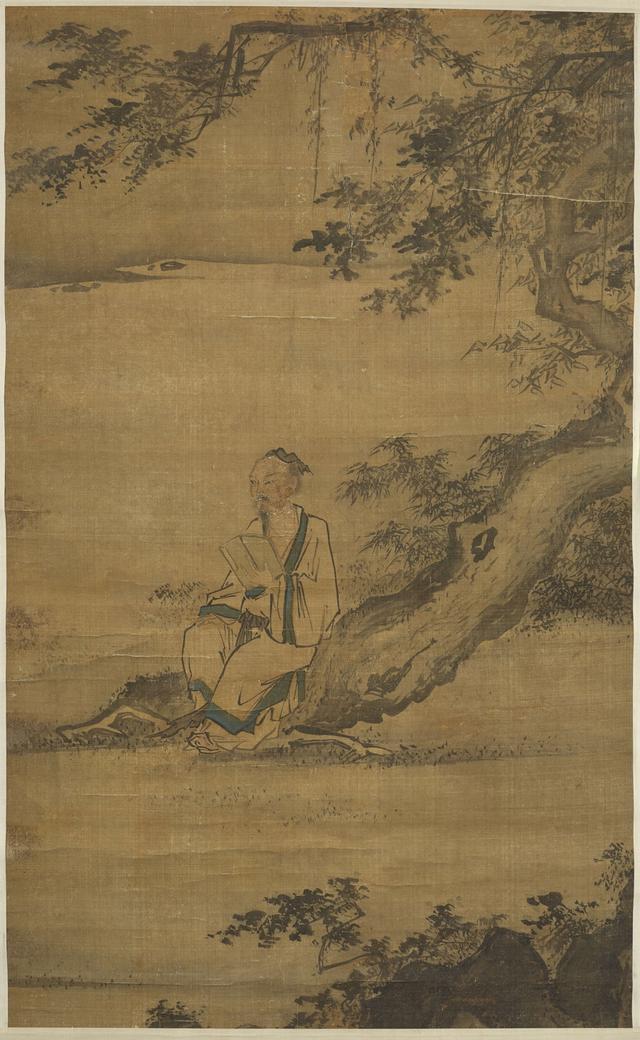
如果说“汉学”的深奥使人看不懂,那么,同为“纯学术”的“宋学”则使人做不到。
“宋学”有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朱熹、陆九渊等代表,对儒学的主张在天理性命。天理之说,近于今天所讲的客观规律,专称“理学”,以程、朱为代表,即所谓“程朱理学”;性命之说,近于今天所讲的主观能动,专称“心学”,以陆九渊为代表,合明代的王阳明为“陆王心学”。但一般“宋学”重在“理学”而不在“心学”。
欧阳修认为,天理性命,为“圣人之罕言”或“虽言而不究”的大道理,“凡所谓六经之所载,七十二子之所问者,学之终身,有不能达者矣;于其所达,行之终身,有不能至者矣”,而“今之学者”舍“古圣贤所皇皇汲汲(可学可行)者”而去“穷圣贤之所罕言而不究者,执后儒之偏说,事无用之空言,此予之所不暇也”。正是《中庸》“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的意思。比如说,什么是道?圣人说:你是仓库保管员,就做好账目;你是畜牧饲养员,就养好牛羊;你是朝廷的官员,就把仁政推行于全国——这些都是每一个相应的人等都做得到的。“宋学”家则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像不扫庭除而扫天下一样,你怎么着手?怎么做得到的呢!《孟子》认为:“位卑而言高,罪也。”大言不惭根本没法做的豪言壮语,是犯罪的行为。章学诚《文史通义》则认为:“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义理以为功,此宋学之所以见讥于大雅也。”
而综观“汉学”“宋学”的两大“纯学术”之儒学,相较于经世致用之儒学,诚如近人周予同先生在《经学史与经学之派别》中所说:“古文学(即汉学)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为考证的,而其流弊为烦琐。宋学以孔子为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载道之具,所以偏重于心性气理,其特点为玄想的,而其流弊为空疏。”这当然很对,却没有指出二者的共同之点,即都是隔离于社会现实的书斋中的学问。
“纯学术”如首饰之于头面,当文化的发展到达一定的阶段,是完全需要的;但过了度,“满头珠翠”可能成为问题。我的这一比喻,是从三四十年前启功先生对我所讲的纯艺术之于社会“如眉之于面,虽不可少而实无用也”而来的。眉毛较之其他四官虽然无所作用,但没有了眉毛,这张脸又怎么能见人呢?“纯学术”之于社会,正如适当的首饰之于头面,虽非必需却能增色。
就这样,儒学由士人经世致用的事业,最后竟变成了学人囿于书斋中皓首以穷的学术。儒学这支箭,在欧阳修们,是用来射国计民生之的;在戴东原们,则是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论证它是“好箭啊,好箭”的。
原标题:《学术,该“经世致用”还是该“出世与超功利” | 徐建融》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栾吟之
来源:作者:徐建融
 晋ICP备17002471号-6
晋ICP备17002471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