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急剧变化的世界,让年轻一代的读者产生了很多新的困惑和焦虑。那么,新一代的年轻小说家会如何书写当前的世界?又如何解答和回应时代的焦虑?
5月18日上午,在阿那亚的蜂巢剧场,香港大学中文学院荣誉教授许子东带着以上问题,向辽京、童末、王占黑、张天翼四位青年小说家提问,大家围绕“21世纪的写作,面对的是什么?”的话题展开了一场丰富生动的对谈。
文学讲述的是生活表面之下的事情,在这里,文字不是记录生活的手段,而是发现生活的手段。小说家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状态。故事写完了,这个身份也就消失了,留下的,是从自己的经历中挖掘出来的,他人无法替代的独特表达。
一个小说家无法与自己所处的时代分割开来,哪怕只是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时代性同样会在自己的写作中显现。毋宁说,这才是小说家与时代产生联结的恰当方式。
01
我的经历,我的故事
许子东:在座四位都是新锐作家,我建议每个人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可以是你听来的、Deepseek找来的,或者是你写的、你将要写的等等。

辽京:大家好,我是辽京。让我讲自己写过的作品,我会有一点懵,我会疑问:这五六年我到底写了些什么?好像我的写作跟我的生活是一个并行关系,在成为母亲的阶段,我写过跟年轻新手妈妈有关的小说;在经历过家中老人离世后,我写下与大家庭情感纠葛有关的故事。我的小说相对来说比较贴近我自己的生活,而因为我过的是非常普通的人的生活,所以可能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
我想讲一件最近发生的、非常切身的事,发生在这个星期四的晚上,我儿子所在的篮球培训班爆雷了,那是一个大型的连锁机构,采取的是预付费模式,然后突然就开不了课了。
我发现做了家长之后,对这种事都很有经验,家长们迅速地拉了一个群来准备维权。这个群首先是一个情绪的发泄,所有人都在说怎么这样子啊,突然就有两个家长,他们相认了,他们说,欸,你怎么也在这?——他们是前两年另外一家钢琴培训机构的受害者,他们的孩子之前是同学,因为钢琴培训机构爆雷,相互失散了。我看到这个对话的时候,我感到,这是一个有点文学的时刻。
整个话语流是有情绪的,资本家如何卷走了我们的血汗钱,他们是怎样的蓄意诈骗,突然冒出两个人,他们在扯家常。我也在这儿,你也在这儿,我们太有缘分了啊。这个“缘分”后面还加了一个哭泣的小表情。
如果这个对话发生在路边,两个老熟人见面,就不会有任何让人觉得有文学的意味在里面,但它被放置在一个情绪很汹涌的话语里,就形成了一种很有意思的对比,虽然很快这个对比就被其他东西冲掉了。但这个对比就是一个文学的时刻,我也喜欢看这样的小说,当两个人经历了千山万水之后,有一个平淡的相遇;或者两个人在日常生活里过着是非常平淡的生活,突然某一天,他们发生了深刻的对话,他们发现了对方在日常生活之外的样子,我喜欢的小说都有这样一种对比,文字不是记录生活的手段,而是能够讲述生活表面之下的东西。
但文字是我们重新发现生活的一个手段。就好像两个人因为培训机构的爆雷失散了,结果他们又因为另一个培训机构的爆雷重逢了,这很有意思,往大了说,这是大的经济环境下一个小的缩影;往小了说,又觉得很温暖,有点好笑的一个小故事。我对文学的看法可能比较传统,我喜欢看这种有对比的、有参差的、有转折的,然后有柳暗花明的叙事,我也想要写出这样的故事。

许子东:很有意思。“战争与和平”,他不写战争,写当中的和平。
张天翼:这个故事让我想到了一本书的名字:《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而辽京老师的这个故事就是:坠落的一切也必将汇合。
童末:当代中国发生的很多现实是比小说还要小说的,有着剧烈的转折。(我想到)北欧社会,它有一种资本主义晚期的氛围,大家生活里已经不再发生类似这样的事情了,他们会陷入另一种文学主题或者情绪中;而我们这代或者是更年轻的一代人,好像有一种“福利”,就是这种事情每天都发生,你只要上网,你一天可能就要追三四个热点。而写小说的人,面对这些事情如何保持自己不麻木,我是没有答案的。
我要讲的故事,与我自己的经验有关。2020年,我做了妈妈,我是在西南一个三线城市的医院里生产的。我从来没有在那里长期生活过,而那边的女性和我们日常接触到的绝大多数女性都很不一样,我遇到了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当我在产检房里等待医生的过程中,我看到护士带着一个即将生产的妈妈进来了,那个女人看上去将近五十岁,她很疲劳,她走路的脚步非常缓慢,当时是夏天,她穿了一件很薄的像老头背心一样的上衣和一双粉色的塑料拖鞋。我注意到她的整个腿和脚都非常地肿,她走的每一步都非常地慢,我感到她很痛。我看着那个护士把她搀到我旁边的妇科待产椅上,向她解释腿要如何分开、架起,但她听不懂。我后来猜测,可能她是少数民族。我又猜测,这位听不懂汉语的妈妈,可能已经生过不止一个小孩,但她依然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正在发生什么,或者她不知道她当时的情况有多危险。因为护士做完检查后,立刻叫了两个医生进来,把她推进了手术室,医生和护士都显神情紧张。我就这样和她错开了。
我开始想象她有什么样的人生,就写了一个短篇,题目很简单,叫《爱的故事》。我写了两个妈妈的相遇:一个是城市里的中产妈妈,很娇气,有一套育儿知识和女性主义的想法,她生完小孩后家人都围绕着她,她可以住到VIP 房间,但她仍然觉得身上各处都痛,恐惧着她的自我的丧失;另一个角色就以我遇到的这个妈妈为原型。我想象她是从村寨逃到了县城,她已经要生产了,她要一个人去面对所有的事情。这个女人从家里逃出来后,她的丈夫就报警了,警察和她的丈夫来到医院,在妇产病房到处找这个女人,他们想把小孩夺回去。我给了她一个非常惨烈的结局:她抱着小孩跳楼了。时间在坠落的过程中静止,她看到了星星,她的女儿刚刚来到这个世界,她对世界的第一次看见,是星空和抱着她的妈妈。这个婴儿并不知道,她马上要面临死亡。

王占黑:你在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想到一个电影,《小家伙》,背景是中亚人在俄罗斯当非法劳工。那些很年轻的劳工很容易怀孕,分娩后为了能继续在俄罗斯留下来工作,会把小孩子送走,所以在这个电影的前面五分之四,都没有那种母与子的关联。她是到最后,因为胀得很厉害,必须让这个小孩把她的乳水吸出来,她是为了自己去做这件事的,但当那个小孩在吸奶水的时候,她突然感到了这种血缘的连结,可她又必须遗弃小孩,所以她边哭边体验了人生第一次哺乳。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辽京:我很喜欢童末的那个结尾,因为我很少有勇气去写一个特别爆裂的结尾,我通常是要么退缩,要么妥协。但童末可以用一种很激烈的死,用这种死亡的方式去回答这个世界。
张天翼:我们经常会处理到死亡和残忍的一些东西,我曾经也和辽京一样,在描述一个七八岁小女孩被成年人性侵的时候,我把整个性侵的过程用童话的方式来表达。现在想起来,会觉得自己怯懦了,因为我在反思一个好的作者是不是在面对这些的时候不能手软、不能心软,一定要去真正地直视那个糟糕的、深渊的东西,你要很诚实地去写,就好像福楼拜写艾玛死的时候,他用了很长的篇幅,我相信福楼拜是爱她的,但是他把那个死亡写得如此的详细,污秽丑陋。李萍儿的死也是。我觉得是不是我们不够勇敢,不敢去处理这个这些东西。
王占黑:我感觉是要直面那个残酷的爆裂,但不一定是要直面这个过程。有时候我们讲一个故事,是把故事藏起来,只看到一个头或者一个尾,或者中间的一个小细节。在生活当中,我们看到很多人的经历,以为得知真相的时候,也只是窥见了真相的一个小小面向,但这个面向足以叫我们清晰地去感知到整个东西是多么残酷和爆裂了。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有一个在外面打工的小男孩,一直联系不到他的哥哥,应该说他的哥哥一直没有跟他联系。隔了一段时间,他的哥哥就会出现了,别人都问他,干吗去了,大家只知道他出国打工了,然后他就一直笑眯眯地说,我去开小店了,生意失败,就回来了。要过很久之后,当公共媒体上广泛地关注到电诈产业和群体之后,大家才知道很多人曾经是主动去打工,然后被遣返的。那你再回过头来想这个谎言,也不是谎言,他只是在敷衍一下,就说我去做小生意,但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足够知道,他是在一个怎样的情境当中了。
童末:我想到了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代表作《宠儿》。那个故事发生在刚刚废奴之后,女主角一路被白人奴隶主追踪,她担心奴隶主抢走自己的小孩,因此在小屋里杀掉了自己的孩子。这是一个真实案件,托妮·莫里森当时只看到了报纸上真实的女主角的照片和一个很简单的案件概述,她在采访者问起这个作品的动机时,说了一句话:当时我对自己说,够了,关于这件事我了解的已经足够多了,我不想像一个记者一样去探究这个案件的整个过程,包括作案的这位母亲的心理。她说,我不需要了。然后她写下《宠儿》,这可能和占黑所说的是相似的。我也会猜想,如果当时她把那个案件彻彻底底地研究了,她会不会被限制,她可能反而写不了她想象出来的那个故事。
许子东:读童末的作品,我搞不清楚这个作家是什么来历,也分不清男女、民族、背景,你想象不到是一个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被训练的知识分子,写出了一个彝族大山里的作品,而且是有人类学价值的,民族之间的,地域之间,她的小说是有《战争与和平》《百年孤独》这种写法的。
02
写作,是一种行动
王占黑:我讲一下跟阿那亚有关的经历吧。我上一次来阿那亚是2020或2021年的时候,一个蛮冷的春天。我很喜欢坐接驳车的副驾驶,我坐了好几趟,发现这个接驳车有一点小问题,它给驾驶员留的空隙太小了,导致驾驶员每次他出来给其他乘客开门的时候,都要想办法扭着把自己挤出来。于是我就下载了阿那亚APP,因为上面有一个叫“马寅信箱”,当时我不知道这个马寅就是CEO,我以为是这个信箱起了个名字叫马寅(笑),我立刻就写了一封邮件,我说希望你们改良一下这个车,没有回音,后来我也就忘记掉了。直到这次来,我一开始也没有想起来我写过这个邮件,是这几天坐接驳车,我还是坐在副驾驶,我感觉好像他们下来的时候要宽松一点了,我不知道是生产车的这个公司主动在更新换代时做了一些改良,还是马寅真的看到了。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我们都要参与进来,参与是为了改变。即使是阿那亚这样一个很多人认为是打卡、文青还愿或者是中产家庭置地的地方,你也还是可以抓住身边的一些小小机会,去实现改变,哪怕这些改变不是因为你产生的。比如我日常还会参与“咸鱼小法庭”,还有“消费者调查”,我都会做,可能这些跟我的写作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说写作也是我们在参与,参与我们正在经历的历史。生活中,很需要大家去做一个多管闲事的人,不管它有没有用。

张天翼:就像那句话,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让世界变成更好的地方。搞文学的人其实会有这种疑惑,我们天天写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呢?有多少人在看?我们改变了这个世界的多少?其实投诉也是一种文体,甚至几个投诉的小段落放在一起,它就可以是一篇小说。
我讲一个跟《如雪如山》有点关系的故事,这本书的第一篇叫作《我只想坐下》,故事发生在长途火车里,有关性骚扰,是我的真实经历。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十八九岁,对于坐长途火车还没有什么经验,夜里,我正趴着睡觉,突然感觉到腿上不对劲,睁开眼睛发现腿上多了一只手,不是我的手,嗯,因为我的手在垫着我的脑袋。这个时候,我面临了一个选择,就是要不要喊,要不要爆发,要不要把他揪出来。虽然我那时候还小,但是也知道一旦喊出来、爆发出来,这个座位可能就坐不成了,可能今晚我也休息不成了。那天我非常的累,非常的困,我当时唯一想的就是,嗯,你不要打扰我,让我把我的觉睡完,所以我就把他的手推开了,接着睡。但是过一会儿又被他摸醒了,我仍然没有爆发,我只是用了更大的力气把他推开。是,几乎是把他的手扔开的,这只手后来就没有再出现在我的腿上了。
这件事情一直梗在我心里很多很多年,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那个没有喊起来的那个人,那就是我。我后知后觉地开始责怪自己,我觉得我非常的懦弱,非常的愚蠢,我这个腿是白给他摸的吗?我妈养我这么大,就是在火车上给旁边人摸的吗?类似这样的责怪,在我心里面滚过了一千句、一万句,我该怎么办呢?
大概在20 岁出头的时候,我第一次以这件事为题材写了一篇小说。嗯,当然那时候写得非常的稚嫩,问题出在这个小说的结尾,我想我该怎么处理这个小说的结尾?我当然不可能让她沉默,后来我是这么写的,你们听了肯定会笑。我把这个摸我腿的人处理成了一个英雄。我写当时火车上会有抢旅人行李的团伙,当这一站快到时,他们就会突然蹿起来,从行李架上抢下很多行李,消失在车门外面。我安排摸我腿的那个人是一个年轻的人,大家知道这里面已经暗含了我对他的原谅,我觉得他像我一样年轻,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自己的欲望,看到一个年轻女人的腿,他就要去摸一摸。被我拒绝之后,他也知错了,当有人抢我的包的时候,这个人勇敢地站出来保护我的行李,被人捅了一刀,倒在血泊中,这故事就结束了。你觉得荒诞吗?

许子东:不,我觉得不荒诞,这是我们很多人处境的写实,我们面临这样的事情,最后常常把它变成一个好像很美好的事情。
张天翼:但是写完这个小说之后,我更加恨我自己了,因为我发现我居然美化他?我不是应该恨他吗,我怎么可以把他写成个英雄呢?那我自己不是更糟糕了吗?再又过了很多很多年,我一直想找到一个方式,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怎么样处理这个故事中的女孩和男孩?最后它变成了《如雪如山》里的第一篇。
我也没有放过那个女孩,我把她写成了一个浅薄、幼稚、天真,还贪图虚荣的人;这个男孩变成了列车员,他非常英俊,长得像刘烨和金城武的混合体,他看到女孩没有座位,一直向这个年轻女大学生献殷勤,把她带到自己的工作间坐下;然后,在这个女大学生放松警惕,甚至萌生出爱意的时候,他的手就摸到了她的腿上;这个女孩子仍然没有叫出来,但她非常坦然,她觉得我就是用这条腿换这个座位,最后我给她安排的结局,是在此后的一生中,她一次一次地面对这些交换,她都换了。当然,这个女孩就不再是我了,因为我知道我不会这样做的。
写完这个小说,我觉得我可以跟这件事情说再见了,我觉得我已经把自己骂了一顿,我也终于把这件事想明白了。它像一个肿瘤,我用小说当手术刀把它切除了,这就是我很多小说的前因后果。
童末:这像是一场自我心理治疗,我会想到我们跟无法切除的东西之间的这种关系,怎么影响我们的写作?因为可能我虽然像许老师说的,我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城市里,但是我其实也因为写《大地中心的人》的一些缘分,现在有一些非常亲密的朋友,他们是在凉山生活或者工作的,其中也有彝族朋友。他们最近几年跟我讲了很多他们经历的事情,包括做公益的朋友,她会告诉我,他们的案主(就是他们公益项目中的帮扶对象),大部分是女性,她们处在非常糟糕的困境里,没有谁比谁更惨,都非常惨。我的朋友跟我讲了一些这样的故事,在她自己工作过程中,她也要去正面遭遇,渐渐地会感到难以承受,却又无法“切除”自己的关切。

我感觉我在写作上,这几年变得“怯弱”了。之前我反而是没有动摇过的,当大家在想写作还有没有意义,文学还能不能起作用,或者它算不算一种行动时,我有过自己的回答,从没有否定过。但当我感觉到了我跟他们,生活境况表面上差异很大的人,其实是关联在一起的之后,他们的处境我看到过了,就没法假装没看见,这些感受,就改变了我的很多认知。我会觉得,我过去的一些写作动机,比如,当感觉到他人的困境可以转化成一个很动人的故事的时候,现在我反而不想去写了。这里面有一些非常晦暗的地方,或者我自己目前还没有办法去说清的东西,或者没法保持恰当的距离。虽然不是我自己的经历,但我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去再现,也不想让它的真实,在再现中反而失去。TA们不只是你作品里的一个处理对象,但是你又必须用一种文学的方式把它很有力度地表达出来,我觉得很难。
03
在“不能说”处往前走一步,就是小说
辽京:我们写小说其实首先是为了自己——当然,图书它是一个商品,是一个产品,它要面对市场、面对读者——但我觉得,就像天翼刚才讲的这个故事,困扰了她很多年之后,变成了一个好像她不得不去处理、不得不写的这样的一个小说;好像我们写作的初衷,至少对我来说,就是为了我自己。写作也好,文学也好,对作者本人的意义其实远远大过于对其他人的意义。我得首先回答我自己的问题,回应我自己的困惑,所以我就想,我每次遇到一些事情,或者我想到从前的一些经验的时候,我会觉得如果这些东西是只属于我的,我只有把它写出来,它才能够变成在其他人那里有所回应、有所共鸣的东西。所以我们不管是性别的经验,还是在这个社会生活中、公共生活中的这个体验或者经验,可能它都是同样的重要,都是同样值得去写出来的。
王占黑:刚刚天翼说“多一只手”,我想到女性所面临的处境里,有时候不只是多一只手,也可能是少一只手,但这些都可以让她们陷入漫长的创伤、自我疗愈、挣扎。
比如朱迪·科默在《初步举证》里的那个视角,她在职场上和一个很帅很有钱的男同事有比较亲密的交往,但是在某一次约会之后,她几乎是在一瞬间知道自己被侵犯了。这是一个独角戏,全程两小时,就她一个人在台上说、台上演。这个瞬间很可怕,她在这个瞬间知道事情越界了。在法庭上,被告律师一直向法官求证的一个焦点是,她有两只手,一只手如果被男性按住,那她另一只手是可以去推开的,然而她没有推开,就说明她是自愿的。被告律师的陈述,让主角也蒙了,她在想说,对啊,我有另一只手,为什么我没有推开?难道我真的不是被迫的吗?主角本身也是律师,她很有经验,但那个时候她也防线崩溃了,一瞬间她意识到了她是两只手被人交叉着扣着的——这个动作非常像耶稣受难,那个时候她就是缺了一只手,所以她什么都做不了。
所以无论是“少一只手”,还是“多一只手”,好像在那个情境当中,你就是一个不仅失语也失能的状态。但在你漫长的回想的过程中,你会一遍一遍地去演练,我怎么发声、怎么恢复我的行动能力,但是那个创伤已经很难再被修补了,因为创伤是一瞬间的真实经历,后面再多的假想都难以补上。所以我觉得,天翼写任何的结局、任何的设定都没有问题,都不要觉得是你自己在合理化或者什么,因为每一步都是自我疗愈,有时候这个疗法是有效的,有时候这个疗法是无效的,有时候你迈出一小步,有时候你迈出一大步,但每一步都是疗愈。

许子东:张天翼讲的这个故事,非常非常典型,说明了文学创作的很多基本规律:一为己,二为国,三不能说,四不能说还要说。
那我来讲最后一个故事:有个将军看到一帮士兵在江边打靶,打得一塌糊涂,将军就走过去说,你们这样打不行,我来打给你们看。将军打了一下,对面报过来,8环,将军说今天是几级风等等之类;然后又打了一枪,7.9环;他瞄准了很长时间,打了第三枪,对面报过来,还是8环。此时这些士兵站不动了。第四枪,他依旧瞄准了很长时间,打过来还是8环。士兵都哗然了,没有人再想听这个将军了。这个时候,将军默默地瞄准了很长时间,打了第五枪,然后说不要报靶数了,把靶拿过来。靶拿过来的时候,全部士兵都惊呆了,将军打了一个五角星。
这个故事影响我半生,我们每个人从一开始都想要打出10环,要进最好的学校,取得最好的成绩,可是很有可能你一开始打出来的就是8环,这样打过两次以后,很多人对自己会有一个标准的降低。而这个故事,我理解是说8环没关系,你只要有自己的追求,你最后打出来的图形永远是独特的,你一生有很多不成功,最后可以变成一个独特的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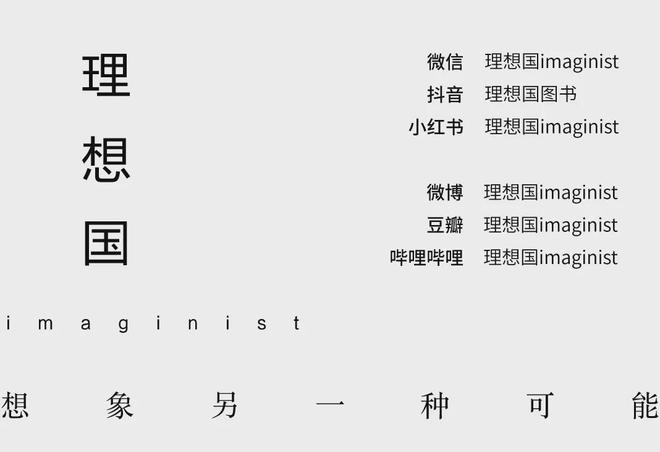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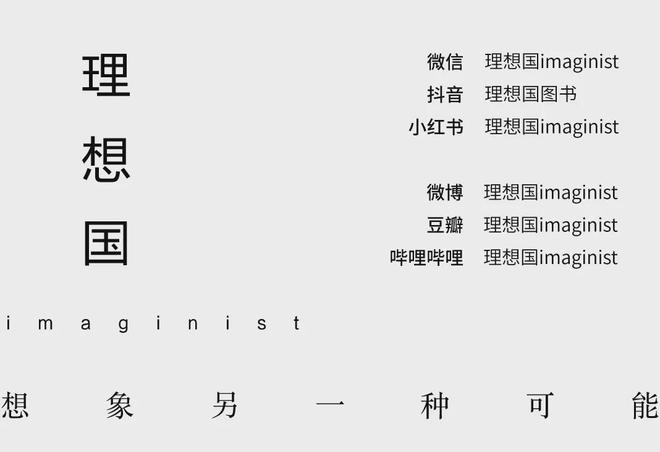
 晋ICP备17002471号-6
晋ICP备17002471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