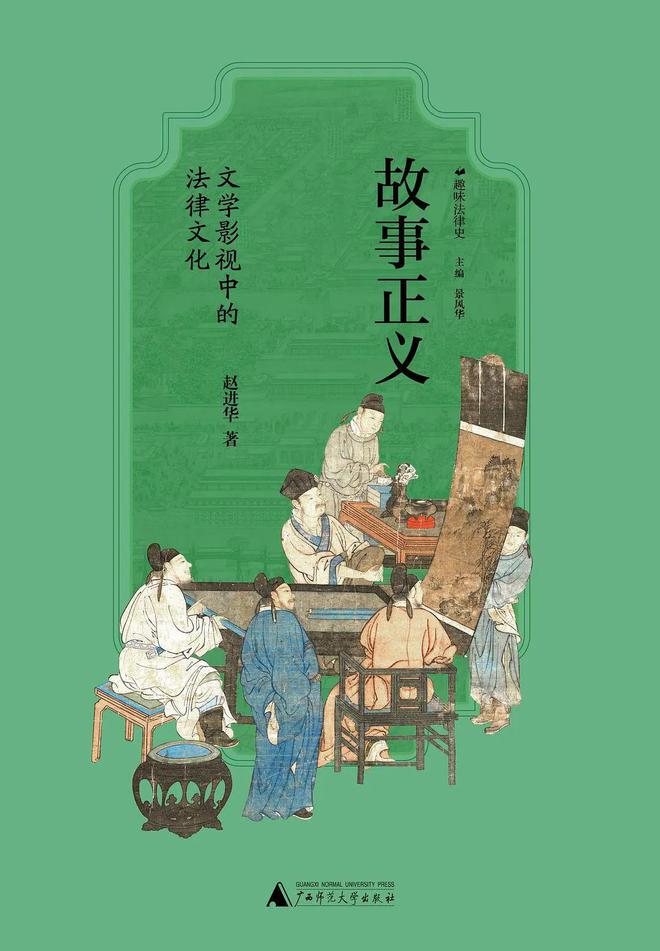
《故事正义:文学影视中的法律文化》
作者:赵进华
版本:广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5年3月
推荐理由:
正义,或许是人们创作故事的动机之一,尤其是以现实为题材的故事,正义更是一个放在故事中进行演绎的主题。毕竟,对故事来说,创作者是唯一的主宰,可以操控角色的命运,让他们由着自己的心意悲欢离合,或生或死,创作者对故事有着近乎造物主的特权,但遗憾的是,这种特权常常并不能被运用,因为故事不仅属于说故事的人,也属于听故事的人,唯有能引起听众读者感同身受,发出共鸣的故事,才能获得长久流传的生命力,而对说故事的人来说,他恐怕也无法跳脱自己所熟悉的时空而随心所欲地创作,即使是鬼狐仙怪的奇幻空间,游侠剑客的不羁江湖,也常常要遵循人间的法则,那些奇幻的法术,玄妙的武功,固然是吸引人的焦点,但也在那最奇妙玄幻的情节展示完后,这些鬼狐仙怪、游侠剑客还是要接受地心引力的影响,重重地落在现实的地面上,接受正义的审判,给出合乎情理的结局。
因此,也就不必奇怪,在《聊斋志异》中讲述人狐异类相恋的《婴宁》中,男主人公王子服与女主人公婴宁相恋时,那位所谓的婴宁嫡母会一本正经地对王子服说:“如甥才貌,何十七岁犹未聘耶?婴宁亦无姑家,极相匹敌,惜有内亲之嫌”——需要考虑中表婚的法律问题。而在侠义小说《儿女英雄传》中,书生安骥同时娶了心爱之人张金凤与侠女十三妹何玉凤,而在婚礼拜堂之后,安家太太老爷却会说出:“讲到家庭,自然以玉凤媳妇为长;讲到封赠,自然以金凤媳妇为先。至于他房帏以内,在他夫妻姊妹三个,‘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我两个老人家可以不复过问矣。”这样听起来似乎“好花并头开”的一夫二妻平等对待的表态,但特意这样表态,反倒让读者意识到,这种家庭内部两位妻子的安排,很可能只是故事创作者的故意设计,而作者本人也知道这样看似公平却并不合法,所以才需要特意说明,才不会让读者觉得不合常理。
上述的两则故事,被赵进华作为《故事正义》开篇的两章,从某种意义上说,有着个中深意,因为它们刚好反映了两种并行的正义观,一种法律上的正义,一种是习俗上的正义。法律正义的判断标准在于是否合法,而习俗正义的判断标准则在于是否合乎约定俗成的习惯——而这恰恰也是传统中国“故事”的另一个定义,也就是过去发生的可以作为惯例沿袭的事例。在崇古观念深远的中国,“古已有之”本就有着强大的权威性。而故事中的“正义”,正要围绕着这两种正义观进行展开。在婴宁的故事中,中表婚的正义性在法律规定、司法实践与习俗观念的三条交错的线上左右横跳。南宋官员从法律的角度指出“姑舅兄弟为婚,在礼法不禁,而世俗不晓”,批评了一些官员在司法实践中“至有将姑舅兄弟成婚而断离之者,皆失于不能细读律令也”,但到元代,却出现了《娇红记》中“朝廷立法,内兄弟不许成婚,似不可违”因此鸳鸯分飞的爱情悲剧——法律的正义与习俗情感上的正义相悖,《聊斋》则是向习俗的正义迈出了关键的一步,造就了一段爱情佳话。《儿女英雄传》中的一夫二妻则是明显地违法行为,一夫一妻才是自古而今的礼法的正义,而一夫多妻制则被视为“乱之本也”,历史上的二妻或是多妻并立,也常常被视为不伦之举,但也同样被沿用下来,甚至“两头大”的婚姻还被视为传奇美谈,流传市井。
在这两则故事中,法律的正义不得不迁就于习俗的正义,两种正义之间的交缠与抵牾,贯穿了全书。故事的正义,也常常要在两种正义观之间寻找平衡。以司法实践为题材的公案小说与影视作品看似遵从了法律的正义,但细读便会发现,这些小说不是凭借一些神异力量或是机巧权术,就是所谓的原心定罪,道德审判,由于中国的小说不善于设计悬疑,在最开始便揭露罪犯的真面目,因此司法实践中的程序正义与律条判例的过程几乎都被完全省略掉了,只剩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基于习俗的正义观。
但故事毕竟是故事,就像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创作者对故事有着近乎造物主的特权”,即使他总是受限于自己所处的时代和习俗,也要顾及读者和听众的感受而不能随意地运用这样的特权,但可以为了他内心的正义以及公众所认可的正义,去让故事变得“正义”。但现实毕竟不是故事,身处现实中的读者与听众,会看到与故事所呈现的正义截然不同的现实。与常识不符的证据和断章取义的证词被用来故意诱导公众的判断力,颠倒黑白常常只需要一纸文书,人们看到与邪恶进行斗争的人下场凄惨,而恶人却得到包庇,而执掌法律的当道却宣布这便是正义。因此,本书越是往后阅读,就越会感到一种深深的挫败与无力——因为,正义常常只能在故事里。
撰文/李阳
编辑/李永博 张婷
校对/王心
 晋ICP备17002471号-6
晋ICP备17002471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