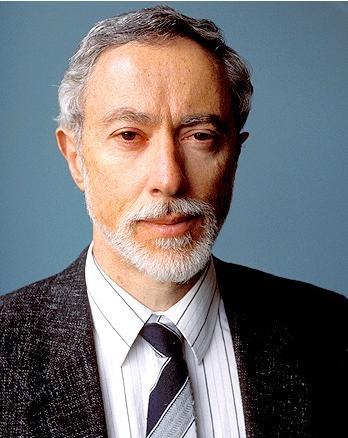
以往都是要等作家挂了之后,我们才能读到他的那些私密信件、日记之类的文献。或者说,当一个人尚在人世时,他的桎梏、自尊心、保护欲都难以使之做出将自己隐私倾泻而出的事(当然维·苏·奈保尔是个特例,他早就将相关资料卖了,然后换回来那本《世事如斯:奈保尔传》),那么读者只能是其作品的读者,对作家的喜欢只能是基于对其作品的喜欢。正如钱钟书所说,“假如你吃个鸡蛋觉得味道不错,又何必认识那个下蛋的母鸡呢?”
私生活可以不探究,但是作家的世界观乃至一己之偏见,并非没有见人的必要。比如那些关于世界、美学、同时代文学、同行、聚会、宗教、性观念、政治,甚至体育比赛和少年懵懂时的记忆,都可以成为津津有味的公共阅读资源。当书信是以这些为内容和目标时,它们进入读者的视野也就顺理成章了。
《此刻:柯慈与保罗·奥斯特书信集》作为两位当代作家的书信集,一位两获布克奖和诺贝尔文学奖,一位拿遍美国大小奖项并数度传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们几乎不涉及任何隐私或者私密生活细节,而是就二人之间的观点和见识展开交锋。换言之,这些书信完全可以看成彼此相互命题的评论文章,在互相吸引、影响、牵引等作用下,各自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台湾将库切译成“柯慈”,因为库切在大陆并非陌生作家,关于他的简体中文版书籍出版已逾十余种,这里就以“库切”相称。
库切有一种对常态事物的无视能力,这个他自己在这本书中也承认过,他说:“我曾骑单车绕遍大半个法国,但得到过的观察都没有什么是耳目一新和值得一提的。”对于常态生活几乎可以等同于生理的自然排斥,那么他对其他方位的生活就一定存在某种异于常人的敏感。他说:“我的经验似乎都是高度个人性质,对别人缺乏意义。在各种独一无二的个别性中找出意义,使之成为一个融贯的系统。”这当然可以看成是库切小说中到处洋溢着冷峻的理由之一,他缺乏对热闹和群体经验的热情。这当然不能说明库切是一个麻烦的人,相反,他只是将他的敏感用在了少数并只能是少数的地方上,并以此集中精力和洞察力。
库切在书信中表达的对人生、对经验、对个人体验、对这个斑杂世界的洞见,都是极为宝贵的,无论对于企图在“小说”这件事上有所念想,还是对于文学读者来说,这些至少是正确方向上的一种有形化理念。而库切对现代文明和所谓的科技进步也有过批判,虽不及法国哲人保罗·维利里奥那般生猛,但也充满了“偏见”和“反动”。
在与保罗·奥斯特就经验探讨时,他这样形容自己:“一个多少有点脑筋的人,他生活在一个旅游极便捷的时代,但到了人生接近尾声之时,他却发现他对可见世界的杂多经验加起来并没有值得一说的,就跟他一辈子都待在图书馆里没两样。”
这是一个让你我这样庸人感到多么不自在的论断啊,当我们积攒薪水和假期,为了那样一个诸如冲绳、巴厘岛、首尔、土耳其、米兰、巴黎的目的地神往和倾注热情时,库切却冷冰冰地告诉我们——并没有值得一说的,那跟待在图书馆没啥两样!
跟冷峻或者说时而多少显得有点恶毒的库切比起来,保罗·奥斯特更为热情和充满活力,从后者总是可以将话题转移到体育运动上来,也能看出来奥斯特的活力,而且他不仅仅是观看,更是要参与其中,这既包括童年记忆,也包括此时此刻的生命状态。
保罗·奥斯特是比库切来说更接近当代审美形式的“文明使者”,这不仅是因为他有过电影编剧和导演的经历(为华裔导演王颖编写电影剧本《烟》,独立执导《桥上的露露》,这些在通信中也有回忆),也是他更加入世和领会这个奇妙斑斓世界的世俗意义。在以往的作品中,保罗·奥斯特是那种可以塑造跟自己完全没什么关系和讲述一个完全虚构故事的作家,比如《在地图结束的地方》、《密室中的旅行》这些,这些似乎是其活力和对世界充满好奇心的另一种证明。
即便有保罗·奥斯特与库切年龄相差近十岁这种事实在先,但跟库切的自认“人生接近尾声”比起来,奥斯特在书信中展现出近似乎超年龄的精力和乐观态度,还是难以令人理解,这大概也跟两人的世俗意义里的处境有关——库切已经是所谓盖棺定论的作家(比如诺贝尔文学奖是所谓的终身成就奖),而他还是在上坡路上不断爬行的小说家。
虽然仅仅是从2008年到2011年间的二人通信,但无论是抱着洞察作家心路历程的目的,包括那些无法形成文章的观点和想法,还是随便考察一下当代作家对当代社会和生活方式的理解和取舍,这本书信集都极好地实现了这些。
 晋ICP备17002471号-6
晋ICP备17002471号-6